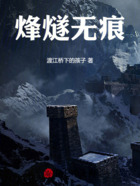
第6章 孙家坳的粥棚
野狐沟的艰险超乎想象。嶙峋的怪石、深不见底的雪窝、盘踞在枯枝上的饿鸦,每一步都像在鬼门关前试探。张十三手腕上那根草绳,成了连接他和柳明远的脆弱命线。柳明远早已没了书生的体面,手脚并用,连滚带爬,棉袍被荆棘撕扯得破烂不堪,脸上手上布满了冻疮和划痕,眼神空洞,只剩下求生的本能驱动着麻木的躯体。张十三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驿卒的筋骨虽硬朗,但连日奔逃、饥寒交迫,身体里的力气正一点点被抽干,胸口那份硬硬的文书,此刻更像一块沉重的冰,不断汲取着他残存的热量。
不知在黑暗中跋涉了多久,当张十三几乎以为自己会带着柳明远一同冻僵在某个无名雪窝里时,一丝微弱却真实的热气混着柴火燃烧的焦糊味,钻进了他冻得几乎失去知觉的鼻腔。
他猛地停下脚步,像一头警觉的獾,无声地伏低身体,示意身后跌跌撞撞的柳明远噤声。拨开眼前一丛挂着冰凌的枯黄苇草,一片小小的谷地豁然出现在眼前。
谷地背靠一处低矮的山坳,散落着几十间低矮的土坯茅屋,屋顶大多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只有少数几缕灰白的炊烟倔强地升起。谷地中央的打谷场上,积雪被扫开了一大片,用泥坯和石头垒砌着一个简陋却冒着热气的土灶,灶上架着一口巨大的铁锅。锅下柴火烧得正旺,橘红的火苗舔舐着锅底,将周围一小片雪地映照出暖色。锅里的东西看不清,但那弥漫开的、混合着粗粮和野菜的寡淡香气,对两个饥肠辘辘的人来说,无异于琼浆玉液。
打谷场上人影晃动。十几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村民,有老有少,排成一条稀稀拉拉的队伍,手里紧紧攥着豁了口的陶碗或木瓢。一个穿着半旧青色圆领袍、头戴黑色幞头的老者站在锅灶旁,身形干瘦,背脊却挺得笔直,像一棵历经风霜仍不肯倒下的老松。他手里拿着一柄长木勺,动作沉稳而缓慢,每一次舀起锅中稀薄的糊糊,都精准地倒入伸到面前的容器里,不多不少。他身旁站着两个精壮的汉子,手里提着削尖的枣木棍,眼神警惕地扫视着谷口和排队的人群,像守卫着最后粮仓的兵卒。
粥棚!张十三的心脏猛地撞击着肋骨。是活路!但这温暖景象的背后,是村民们脸上挥之不去的麻木与惊惶,是那两个村丁棍棒上折射出的寒光,是空气中弥漫的、比寒气更刺骨的紧张。
“是…是活人!有吃的!”柳明远也看到了,眼中爆发出狂喜的光芒,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响,下意识地就要往前冲。
“站住!”张十三一把扣住他的胳膊,力道之大,让柳明远痛呼出声。张十三的眼神锐利如刀,压低声音,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想死你就喊!看看他们手里的棍子!看看他们的眼神!”
柳明远被他眼中的厉色吓住,顺着张十三的目光看去。果然,打谷场边缘,一个原本在雪地里玩耍的半大孩子看到了苇草丛后冒出的两个“野人”,吓得哇一声哭出来,躲到了大人身后。这一下,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排队领粥的队伍骚动起来,惊恐的目光齐刷刷投向谷口方向。那两个持棍的村丁立刻上前一步,挡在锅灶和老者的前面,棍尖抬起,直指张十三和柳明远藏身之处,口中厉声喝道:“谁?!出来!”
老者——孙老丈,也停下了舀粥的动作,浑浊却异常沉静的目光穿透风雪,落在张十三脸上,带着审视,没有立即喝骂,却比棍棒更让人心头发紧。
短暂的死寂。风雪似乎也屏住了呼吸。张十三知道,下一步棋,关乎生死。
他深吸一口气,那口气带着雪地的冰冷和肺腑深处的灼痛。他缓缓松开柳明远,示意他待在原地别动,然后,独自一人,慢慢从苇草丛后走了出来。他刻意放慢脚步,让每一步都踏在雪地上发出清晰的“咯吱”声,显得笨拙而无力。他没有举起双手——那会显得心虚——只是将双手摊开在身体两侧,掌心向上,展示着空无一物。
他一步步走向打谷场,目光越过那两个如临大敌的村丁,径直落在孙老丈脸上。距离锅灶还有十步远时,他停下了。这个距离,既表示没有威胁,又足以让对方看清自己的狼狈与坦诚。
“老丈安好。”张十三的声音嘶哑干涩,却努力保持着一种底层人见小吏时特有的、混杂着恭敬与卑微的平稳调子。他微微躬身,行了个极不标准的叉手礼——那是驿站里见往来小吏时学的皮毛。“小子…邢州驿火长张十三,遭了兵灾,驿站毁了,带着…带着个落难的读书人兄弟,迷了路,实在冻饿得走不动了…瞧见老丈这儿有口热乎的,斗胆…斗胆来讨口汤水,暖暖身子。”他刻意点出了“邢州驿火长”这个早已失效的身份,这是他在乱世中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勉强能与“秩序”沾边的凭证。同时,他把柳明远说成“读书人兄弟”,而非累赘,也隐含着一丝希望——读书人,在这乱世,对某些人或许还有一点点价值。
孙老丈没说话,那双深陷在皱纹里的眼睛像两潭古井,波澜不惊地打量着张十三:破烂不堪却依稀能辨出制式的驿卒号衣外裹着不合身的粗布袄,冻得发青的脸颊上刻满风霜,嘴唇干裂出血口子,脚上的靴子磨得露出了脚趾,但那双眼睛…虽然布满血丝,深处却藏着一股驿卒特有的、认路识途的韧劲儿和一丝极力压抑的警惕。他又瞥了一眼远处苇草丛边探头探脑、形容更加不堪的柳明远,那身破烂的儒衫和脸上未消的淤青,印证了“读书人”的身份。
空气仿佛凝固了。村民们紧张地屏住呼吸,两个村丁的棍棒依旧指着张十三,只等孙老丈一声令下。
孙老丈的喉结滚动了一下,终于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是长期发号施令养成的习惯:“火长?邢州驿…离此地可不近。驿站如何毁的?兵灾…是哪一路的兵?”
问题像冰冷的锥子,直刺要害。张十三心头一凛,知道考验来了。他不能细说阎罗刀屠驿的惨状,那会吓坏村民,也可能暴露自己身负情报的危险。他只能含糊,带着底层人面对官府盘问时的惶恐与无奈:“回老丈…是…是叛军!安禄山的兵!黑压压一片,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小的和几个兄弟冒死逃出来…就…就剩我们俩了…”他声音发颤,适时地低下头,掩饰眼中瞬间涌起的真实悲愤和恐惧。他搓了搓冻僵的手指,指节粗大变形,那是常年握缰绳、搬驿袋留下的印记,比任何言语都更能证明他的身份。
孙老丈的目光在张十三那双驿卒特有的手上停留了片刻,又扫过他脸上那种混杂着恐惧、疲惫和一丝卑微恳求的复杂神情。乱世之中,真真假假早已模糊,但这双手,这身破烂的号衣,这提到叛军时本能的恐惧,做不得假。至于那“火长”身份是真是假,此刻反而不重要了。
他沉默了几息,时间长得让张十三后背渗出冷汗。终于,孙老丈手中的长木勺再次动了。他没有立刻给张十三粥,而是对身旁一个村丁吩咐道:“柱子,去,把那边的后生也扶过来。瞧着快不行了。”
柱子愣了一下,看看孙老丈,又警惕地瞪了张十三一眼,才不情不愿地放下棍子,走向苇草丛边几乎瘫软的柳明远。
孙老丈这才看向张十三,目光依旧沉静,却少了些审视的锐利,多了点不易察觉的悲悯。“过来吧,张火长。”他指了指灶旁一块还算干燥的石头,“天寒地冻,先烤烤火。粥…是朝廷赈济的,稀是稀了点,能吊命。”他刻意强调了“朝廷赈济”四个字,像是在提醒自己,也像是在维护这摇摇欲坠的秩序中最后一点名分。
“谢…谢老丈!”张十三心中巨石落地,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涩和暖流猛地冲上眼眶,被他死死压住。他依言走到石头边坐下,不敢离那锅珍贵的粥太近。灶膛里跳跃的火焰散发出真实的、令人几乎落泪的暖意,一点点驱散着透骨的寒气。他贪婪地汲取着这丝温暖,紧绷了不知多久的神经终于得到一丝微弱的松弛,身体里冻僵的血液似乎开始重新流动,带来一种近乎虚脱的疲惫感。
柳明远被柱子半扶半拖地带了过来,几乎瘫倒在张十三脚边。孙老丈亲自舀了半勺稀薄的糊糊,倒进一个破陶碗里,递给柳明远。柳明远双手颤抖着接过,也顾不上烫,也顾不上什么斯文,像濒死的野兽般埋头猛啜起来,滚烫的糊糊烫得他直抽气,却舍不得停下。
孙老丈又舀了同样分量的一碗,递给张十三。张十三双手接过,粗糙的陶碗传递着暖意。他看着碗里几乎能照见人影的稀粥,几片不知名的野菜叶漂浮其上。这碗清汤寡水,在驿站鼎盛时,连喂马的马夫都未必看得上,此刻在他眼中却重逾千斤。他没有立刻喝,而是抬起头,再次看向孙老丈,声音低沉而真诚:“老丈大恩,没齿难忘。”
孙老丈摆摆手,没说什么,继续给排队的村民分粥。打谷场上紧张的气氛缓和了一些,但村民们的目光扫过这两个外来者时,依旧充满了疑虑和不安。那两个村丁也回到了原位,棍子虽然放下了,但警惕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他们。
张十三小口啜饮着温热的糊糊,粗糙的颗粒刮过干裂的喉咙,带来一阵刺痛,却也带来一种活过来的真实感。他一边喝,一边用眼角余光不动声色地观察着这个小小的村庄:低矮的土墙大多有修补的痕迹,村口设置了简陋的拒马,几个半大孩子拿着削尖的木棍在结冰的河沟旁巡逻。这里并非世外桃源,而是在惊涛骇浪中勉强维持不沉的一叶扁舟。孙老丈,就是那个掌舵的倔强老船夫。
一碗薄粥下肚,身上终于有了一丝热气。柳明远也缓过一口气,捧着空碗,脸上恢复了一点血色,虽然依旧狼狈,但眼神里有了点神采,他挣扎着想向孙老丈行礼道谢,被孙老丈制止了。
“后生,省点力气。”孙老丈看着柳明远破烂的儒衫,问道:“听口音,不是本地人?读书人?”
“晚…晚生柳明远,范阳人士。”柳明远声音虚弱,努力挺直了些腰背,“家父…曾在县学任教谕。叛军起事,阖家南逃…途中失散…”提到家人,他眼圈又红了,声音哽咽。
“范阳…安禄山的老巢啊。”孙老丈叹了口气,脸上的皱纹似乎更深了,“能逃出来,不易。”他不再多问,乱世之中,谁家没有一本血泪账?
就在这时,一个负责在村口瞭望的半大小子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脸上带着惊惶,凑到孙老丈耳边急促地低语了几句。孙老丈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握着长木勺的手背青筋微微凸起。他猛地抬头,目光如电,扫过张十三和柳明远,那眼神复杂难辨,有警惕,有忧虑,甚至有一丝…决绝?
张十三的心瞬间提了起来,握着空碗的手指微微发白。他顺着孙老丈的目光,下意识地望向村口方向。远处,通往官道的山梁上,似乎有几道模糊的黑影在移动,速度不快,却带着一种令人不安的压迫感。
短暂的喘息结束了。新的阴云,正沉沉压向这山坳里最后一点微弱的暖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