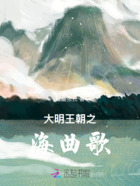
第2章 乞巧重逢
【嘉靖三十三年七月初七,1554年】
【一年前】
【青州府张宅】
“昭宁。”她听到有人唤她,声音清透,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月光像融化的银,静静淌在涛雒盐场的卤池上。张昭宁赤足踩在盐板上,细碎的盐晶硌着脚心,却不觉疼痛。远处传来熟悉的脚步声——一个少年披着补丁摞补丁的短褂,从雾里走来。
当她伸手触碰时,指尖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他的温度。少年的手掌粗糙而温暖,带着常年劳作的茧子,却让她莫名安心。他轻轻一拽,昭宁便跌入他的怀中。
“你...”她的话被他的唇堵住。这个吻带着咸涩的味道,像是海风与盐粒的混合。他的手抚过她的发丝,指尖缠绕着那些散落的青丝,如同潮水轻抚沙滩。
“别怕。”他在她耳边低语。
“别走!”昭宁她猛地从榻上坐起,冷汗浸透了中衣。
“小姐,卯时三刻了。”妙音端着铜盆进来,盆中的清水晃出细碎的波纹,“该起来梳妆,用了早食还要去‘冰壶轩’听讲。”
昭宁怔怔地看着腕间的镯子,梦中残留的咸涩似乎还留在唇齿之间。她突然捂住滚烫的脸——自己怎会做这般荒唐的梦......
晨时刚到,昭宁已端坐在‘冰壶轩’的紫檀大案前,她指尖在算盘上噼啪连响,鎏金虾须镯随着动作轻晃,在账册上投下细碎的光斑。账房先生周墨捋着山羊须,眯眼瞧她。
“一百四十二两五钱八分。”昭宁脆声答道,算珠最后一响恰落在她报数的尾音上。
“大小姐这'飞归'越发精熟了。本银百两,月息三分,按《算法统宗》复利计之,正该是这个数。”
周老爹眼里闪着欣慰的光,山羊须随着笑意微微颤动:“当年你父亲在这个年纪,还只会拨'九归'呢。”
“哈哈哈哈!”一阵爽朗的笑声从门外传来。张继棠大步迈进门槛,沉香色直身被晨光镀上金边,腰间蹀躞带上挂着的和田玉佩随着步伐轻轻晃动。“爹爹不及宁儿聪慧,”他抬手轻抚女儿发顶,“宁儿早慧,知道替为父分忧,为父甚是欣慰啊!”
万延芬手捧青瓷盏缓步随入,她腕间缠着的那串菩提子随着动作轻响——每颗珠子上都刻着细密的“水月观音”梵咒,这是她每日在佛前诵经时摩挲的念珠。
“宁儿昨夜看账到三更,今儿乞巧节,就免了这半日的课吧...”她将描金请帖轻轻放在紫檀案头,帖上泥金小楷映着晨光,“你舅母差人来请,说是乞巧宴的席面都备好了...”
“娘!”昭宁一把拽住母亲袖角,鎏金虾须镯在腕间叮当作响,“舅母家的乞巧宴年年如此,左不过是些投针验巧的闺阁把戏,甚是无趣。要么就请了八音班,年年都奏《百鸟朝凤》《将军令》这些曲子,女儿想和婉姐儿去醉仙楼...”她眼波流转,忽地压低声音:“听说那儿来了一个新的说书先生,专讲《水浒》话本,甚是有趣。”
“什么?!”万延芬手中菩提子“啪”地拍在案上,“一群未出阁的小娘子去酒楼听这些不堪入耳的话本?这些年你跟着七叔公学做生意,《女训》、《烈女传》不读也就罢了,如今越发...”
“娘~!”昭宁拖长声调,指尖在账册上轻点,“家中无长兄,弟妹尚且年幼,女儿不替爹爹分忧,难道要眼睁睁看着盐引被那些胥吏盘剥去了么?”
提到家中无长兄,却也戳中了万延芬的痛楚,这些年她始终没有为张家诞下儿子,张继棠年逾四十才纳一妾,如今庶子女才刚5岁。
“可是你舅母那边三番四次来请,你表兄万振林…”万延芬还要再劝,却被丈夫抬手止住。
“不妨事。”张继棠捋着短须笑道,“醉仙楼二楼的'听雪阁'早包下了,专供女宾聚会。”他转向妻子,声音温和却不容置疑:“那雅间临街挂着湘妃竹帘,三面围屏,即便是衡王府的官眷也会过去听曲。”忽又正色对女儿道:“明日开始,让赵干办教你《盐政利弊考》...”
“女儿遵命。”昭宁福身行礼,又向周老爹、母亲匆匆施礼。转身时藕荷色马面裙翻飞如蝶,虾须镯撞在门框上“铮”地一声清响。妙音抱着妆花缎披风急追出去:“小姐等等!轿子还没备好...”
万延芬望着女儿远去的背影,手中菩提子转得急了些:“老爷,昭宁毕竟是个女儿家,如今就要及笄,该为她许个好人家。你让她终日学习经商,抛头露面,但她终究不能继承这份家业,倒不如待荣儿大些了...”
“荣儿才开蒙,连算盘珠子都拨不利索。”老爷打断了万延芬,“岂能和我们的宁儿相比,她八岁就能背《盐法条议》了!”。
“那既如此,何不找一贤胥,入赘我家。”
“你又打算万振林?那小子连县试都没考过,待到有功名在身,再议不迟。”张继棠继续说道:“宁儿从小就乖巧懂事,如今她与那瑞蚨祥的孟家姑娘,德寿堂的周家姑娘,王家酱园的王家姑娘交好,对我们海隆盐号也无坏处,平日她想做什么,就由着她去吧,她知道分寸。”说罢,叹了口气望向窗外。
不多时,昭宁的轿子便停在“瑞蚨祥”的描金匾额下。她轻提裙摆跨过门槛,径直往右室走去——这间专供衡王府采办的雅室,平日陈列的都是金丝蟒袍、云锦妆花之类的贡品,寻常客人连看都不得看一眼,倒成了她们闺蜜四人说私房话的好去处。
“宁姐儿来得正好!”苏婉从一匹流光溢彩的纱罗后探出头,眉眼弯若新月。这位瑞蚨祥家的千金性格和顺,平日里最喜欢钻研织功技法。她指尖轻抚过纱面,金线在日光下泛起粼粼波光:“你瞧这新到的柞蚕丝纱——金线入纬三十二道,轻薄得能透出手指影子。“
“咱青州府特有的柞蚕丝,配上你们瑞蚨祥密不外传的织纱技艺,价倍杭罗,一纱难求。前些日子你帮我留了一匹,父亲送去给那提举的老母贺寿,哄得她不甚欢喜!”
昭宁一边说着,一边执起一角对着窗棂细看,她不由惊叹:“青州纱本就轻若烟雾,再织入金线,竟似将一泓秋水凝在了缎面上。你家织工这手艺,怕是应天府织造局的老师傅也未必及得上。“
苏婉突然耳根飞红,忙不迭将料子卷起:“哪、哪有什么巧的,不过是个寻常织户...“声音渐低如蚊呐。昭宁正自疑惑,忽听珠帘哗啦一响。
德寿堂的姝姐儿风风火火闯进来,贴身丫鬟墨香抱着个鎏金锦匣,跑得钗环都歪了。“可算截着你们了!”她一把拽住两人袖角,“今儿不去醉仙楼,我带你们去东关街。”这乞巧大集已经摆了三天,好不热闹!”
见二人迟疑,姝姐儿神秘一笑,还有“东关番货行都没有的稀罕物!”
“东关番货行连暹罗的龙涎香都有...”昭宁蹙眉。
“还有朝鲜的千年参!琉球的螺钿!”苏婉接道。
“琉球的螺钿算甚么?这个才是真宝贝——“她压低声音,从袖中抖出张洒金帖,”乞巧街新到了批番邦秘戏图,画的是...”
话未说完,昭宁已红着脸去捂她的嘴。三人笑闹着上了轿,不多时便到了东关街。“这真是比平日热闹十倍!”昭宁不由得感叹。
旋煎羊白肠在铁鏊子上滋滋作响,冰雪冷元子盛在琉璃盏里,像捧着一汪凝固的月光。糖画老叟手腕翻飞,金黄的糖浆顷刻化作振翅的凤凰——正是时兴的《百鸟朝凤》花样。
台上杂耍人正演到“七仙渡河”,青衣的何仙姑踩着高跷,手中的莲花灯突然喷出三尺高的火焰。围观的人群哗然,铜钱如雨点般掷向台面——这是要“点戏“的规矩。
“今年的确多了不少番帮物件。”昭宁呢喃着,在一处珠翠摊前驻足。那玳瑁梳簪镂空雕着并蒂莲,簪头还嵌着颗罕见的血珀,“的确精巧,只是…莲瓣纹样曲折回环,与中原制式大不相同。”
“小娘子一看就是个识货的主儿,这是暹罗来的样式,那边管这叫'夜合莲'”摊主四下张望,突然压低声音:“......若想要看看新奇的?”说着,他神秘兮兮地从柜台下拿出一锦盒,打开后,又猛地掀开苫布——“这才是真宝贝。”
“一把折扇?”昭宁拿起扇子,在阳光下倏地展开。扇面金粉簌簌而落,透雕的浪花纹在光影间流转,竟似活物般粼粼闪动。
“姑娘,”商贩声音沙哑,“这松浦家的手艺,整个大明怕也难做出这样的扇子。十两银子...”
“十两!能买足足五匹青州纱。五两银子,我还能勉强考虑考虑。”昭宁把玩着扇子。这商贩嘴角一抽正要还价,“啪!”一只骨节分明的手突然按住扇面。来人一袭靛蓝直裰,作商贾打扮,可虎口厚茧与挺直的脊背,却掩不住行伍之气昭宁一惊,抬眸对上一双冷冽的眼。
“青州地界,怎会有倭货。”他声音不大,却让商贩瞬间面如土色。
话音未落,四个身着短褐的壮汉已围上前来。见商贩要跑,这商贾打扮的人一脚踢翻摊位,张昭宁被一把腾开,几个踉跄才站稳。摊位的木架散落,首饰钗环掉了一地。
“放肆!”昭宁不明觉厉,一股火冲上来,正要上前发作,姝娘猛地拉住张昭宁的衣袖,凑到她耳边急道:“别冲动…此人身上有我德寿堂特供的青州白药味,他们应该是安东卫的人。”
“安东卫的人?”昭宁思索着,还未想出个头绪。只见那为首的汉子掏出麻绳,手法娴熟地将商贩双臂反剪,押在地上。一时间,街市的人一阵骚动,都围观过来。
“姑娘可知《大明律》有载,”那商贾打扮的男子声音冷冽,一边说一边拨开人群,径直向昭宁走来。“凡私贩倭货者,主犯绞刑,从犯流三千里——购买者亦当杖八十,徒二年。”
他目光如刀,直刺昭宁面门,“小娘子方才可是要买这倭扇?”
昭宁心头一跳!这扇竟然还在自己手中,她只觉这扇精巧,却不曾想这是倭扇。但她不肯示弱:“这位大人好大官威!”她扬起下巴,继续说道,“我张家世代经商,也涉海贸,市舶司的勘合文书年年验看,何曾见过这等荒唐条例?”
男子冷冷地回道:“嘉靖二十七年颁《防倭敕令》,白纸黑字写着‘凡倭国金漆器、描金扇等物,皆在禁绝之列’。”
此时,婉姐儿被吓得说不出话。姝姐儿急忙扯昭宁衣袖:“宁姐儿别争了!去年即墨陈家的小姐,就因买个倭国胭脂盒,她父亲打点了好些人,才被罚了二十两银子了事...”
“既是商贾之女,更该明白通倭之罪!”那商贾打扮的男子步步逼近,山文甲在衣袍下若隐若现。
“大人明鉴,买卖之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钱货两讫,方成交易。“她目光灼灼地盯着那军官,“如今钱未过手,货未交割,如何能定我买卖之罪!”昭宁心里慌乱,但还是争辩道。
“大人!那小姐方才分明给了小的十两银子买这倭扇!”
那被按倒在地的商贩突然嘶声叫嚷起来,额角青筋暴起,活像条被扔上岸的鲶鱼,拼命扭动着身子。
昭宁呼吸一滞,“你这厮竟然攀诬我!”
“购买倭扇,形同资敌,小姐若不知就随我回石臼所走一趟。”
“大人,你不可以带走我们小姐,待我秉明老爷...你...”妙音强撑着护在小姐身前。
正在僵持之时,“大人容禀。”一道沙哑的声音突然从鱼摊后传来。只见个戴斗笠的高大男子单膝跪地,看不清脸,粗布短打裹着虬结肌肉,露出的手腕上满是白痕。他声音沉稳:“这商贩方才说收了十两银子?”
昭宁闻言立刻会意,冷笑一声,从妙音手中接过绣着缠枝莲纹的荷包,将里面的银钱尽数倾倒在青石板上,“大人请看,这些可都是成色十足的纹银,每一块足足五两。若真如这奸商所言,我已付了十两银子...大人不如搜搜他的身,一看便知。
为首的军汉逼近那商贩:“你兜里可有十两纹银?”他猛地扯开商贩的褡裢——几块散碎铜钱叮叮当当滚了一地,最大的不过三钱重。“大人,都是些潮银劣钱,连五两都凑不出。”
那商人装扮的男子——实则是安东卫佥事王承宪——他若有所思地瞥了眼灶生。今日,本是命他潜伏在乞巧街市查探倭寇线索,为何会突然为这女子开脱?正当疑惑之际,他目光落在昭宁腕间的鎏金虾须镯上,似乎忆起了什么,瞳孔微缩。
“罢了,”王承宪突然收剑入鞘,“今日就不与你为难了。”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昭宁一眼,“如今倭患猖獗,姑娘日后采买还需多加小心。”说罢一挥手,带着被捆缚的犯人转身离去。
“小姐——”只见不远处雷教头挤过人群,粗布衣裳被汗浸透。这位安东卫退役百户,如今只能在张府当个护院教头。他望着被押走的倭贩,眼中闪过一丝不甘——若是当年在卫所,这等功劳岂会落到旁人手里?
“醉仙楼寻不见您...”他话音未落,就被昭宁打断:“你怎么才来,我方才差点被这安东卫的人当成通倭的犯人缉走,爹爹养你们这些护院有何用?“昭宁累积的无名火没处撒,被雷刚触了霉头。
雷教头喉结滚动,拳头在身侧捏得发白。十年前他在灵山卫杀倭立功,如今却要受这黄毛丫头的呵斥...“是某的过错。”雷刚无奈地抱拳应声。
“宁妹妹莫怕!”一声暴喝骤然炸响,惊得街边摊贩手上一抖。只见一男子,身着湖绸直裰,腰间蹀躞带上的玉佩叮当作响,挥拳便朝那商贾打扮的男子袭去。
“哟,这不是永昌号的少东家赵大公子么?”程家小姐以团扇掩唇,眼波流转间尽是揶揄,“莫非是闻着宁姐儿的脂粉味儿,一路从永昌号追到这儿来了?”
王承宪身形未动,只抬手一挡,腕间暗劲迸发,震得赵明远踉跄后退三步,险些撞翻一旁的糖人摊子。“再敢妨碍公务,”他声音冷冽如腊月寒冰,“休怪本官将你一并锁拿。”
赵明远顿时面红耳赤,讪讪退至一旁。昭宁只觉今日事发突然,一波刚平,又见这纨绔来纠缠,只觉额角突突直跳。
昭宁唤来妙音,对着她耳语一番,妙音会意点头,昭宁说罢,也未唤轿夫,转身溜进偏巷,身后传来赵明远的呼喊声:“宁妹,等等我!”。
昭宁穿过两条窄巷,见赵明远的喊声听不见了,才放缓脚步,理了理微乱的裙裾,沿着护城河慢行。
酉时的日头斜挂在城楼飞檐上,将她的身影拉得老长。河水映着晚霞,泛起金红色的波光。昭宁整了整松散的鬓发,忽见水中倒影里的自己——只觉自己狼狈不堪,藕荷色马面裙并不像平日那般艳丽好看了。
她懊恼地甩甩手,回想起刚刚的情形还觉后怕:“《防倭敕令》颁了这些年,何曾见当街搜检?安东卫的人竟还换装暗访,如此大费周章。”
她盯着河面漂浮的柳絮,突然想起那军官甲冷冽的眼神,“若真被押去石臼所...爹娘还不知道有多担心。那安东卫的人着实可恶,长到这般大还没人这样的威吓我;还有…那鱼贩,竟突然开口为自己说话;但那军官似乎认识这鱼贩。哎都怪姝姐儿那家伙说要来这乞巧街市,现在去醉仙楼听话本的兴致都没了…”
酉时的钟声从城楼传来,惊醒了她的思绪。昭宁拎起裙角,踏着暮色往张府疾步走去。
行至府邸,暮色已浓。昭宁正欲推门,忽见——
那个戴斗笠的鱼郎,正抱着稚童站在角门处。身旁立着的,赫然是方才抓人的“商贾”!那“鱼贩”斗笠微微抬起,露出一张俊朗的面庞。脚边的竹筐里,整齐码着用蒲草捆好的鳓鱼鲞。
“好啊!”昭宁指甲掐进掌心,“他俩果然认识。”
孙管家迎着昭宁从正门进来,此时,暮色已经染红了檐角的脊兽。“这角门连着庖厨,他俩来做甚?”昭宁一边想着一边匆匆她从前厅穿过垂花门想去看个究竟。
“姐姐回来了!”乳娘正带着昭荣、昭慧在院儿中玩耍,荣哥儿见了昭宁忙扯着小妹昭慧颠颠跑来行礼。昭宁随手揉了揉荣哥儿的发顶,目光却越过他们,直往角门方向瞟去。
崔小娘闻声从膳堂出来:“宁儿怎么这个时辰回来了?用过晚食不曾?”
“用过了。”昭宁随口敷衍,脚步不停往厨房去。
膳堂里只点着两盏羊角灯——母亲带着贴身仆妇去了舅母家赴宴,如今只剩崔姨娘陪着老夫人用膳。老夫人正低头木讷的扒拉着碗里的东西,眼皮都没抬。
“小姐怎么到庖厨来了?”厨娘王妈妈放下手上的活儿,在围裙上擦了擦手。
妙音提着裙子迎了过来:“小姐,可算回来了!见昭宁四下张望,“您这是......”
“方才那两个人呢?”昭宁推开角门往外张望,“不对,是三个——还有个孩子。”
妙音:“他们放下鱼就走了。小姐吩咐我赏那渔贩十两银子,他死活不肯收。最后还是王大人——就是那个要绑您的官爷——说权当是买鱼钱......”
昭宁一怔:“十两银子,可抵他这鱼贩半年嚼用,他竟不收。”又问道:“他俩怎会相识?
“那位商贾根本不是商贾,是安东卫的王佥事王大人,专程来查倭货走私的的。至于那鱼贩......他也根本不是鱼贩,而是涛雒盐场的灶户,”妙音顿了顿,“说是灶户也不能算是灶户,如今被王大人征作盐兵,专在暗处查探线索。“
“什么商贾鱼贩官兵灶户的......”昭宁听得头晕,但也知道了其中究竟,“那孩子呢?”
“这倒没细问,许是那灶户家的娃娃?”妙音心不在焉的答道,一边帮着王妈妈腾挪厨房的菜。
王妈妈突然从鱼筐里捧出两条鳓鱼鲞:“小姐您瞧,这可是顶好的'天字鲞'!”
油纸包裹的鱼鲞足有一尺二寸长,银鳞如新,鱼尾完整。厨娘粗糙的手指抚过鱼身:“三月里的'春鳓'最是肥美。”
“你懂得倒多。”昭宁忍不住打断。
厨娘讪讪住口,突然又红了眼眶:“小姐怕是忘了,老奴是从莒南老宅跟过来的。您小时候最爱吃我做的鳓鱼蒸蛋......“说着突然拍腿,“明日就用这鲞配上燕窝、鹿筋炖个上汤!”
咕——
昭宁的肚子突然叫出声。她尴尬地咳嗽:“妙音,添副碗筷,我陪祖母用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