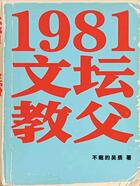
第19章 浪头
杨百川并不在意张虹的背叛,也没打算去问她。
他现在有大好的时光,哪能把日子虚耗在一个女人身上?
当务之急,还得是多写几部作品出来。
后头几天,他都窝在宿舍里,一门心思改《潮生》、写《雾镇》,连张虹那场改稿会也懒得去了。
后来他听人家讲,那篇《马嵬》被批得很惨。领导说,现在是社会变革的节骨眼,放着这么多现实题材不写,偏要整些古代爱情故事,扭扭捏捏的,一点格局都没有。
而且也没有余启东、牛红旗这样的人站出来替她说话。
张虹在会场上哭得梨花带雨,捂着脸就跑出去了。
杨百川听了这些,心里多少有点不忍,眉头皱了皱。
不过倒不是心疼张虹被人围攻,而是可惜了那篇好稿子。
《马嵬》确实写得不错,不该遭这样的待遇。他心里有种同病相怜的滋味。
李小棣是在两天之后回来的。
听杨百川讲完改稿会的事儿,李小棣冒火:
“他们没得眼水,看不懂好文章。就是因为这些老果果还待在文坛,占着茅坑不屙屎,我们的品味才这么低级!”还说要是他在场,一定会蹦起来大骂特骂。
可转念一想,批评杨百川的人里,还有他的顶头上司,《巴蜀文艺》的主编,立马就不吭声了。
李小棣这次回去,帮忙筹划了一个文学比赛,这也是他带给杨百川的好消息。
作为川省数一数二的文学杂志,《巴蜀文艺》自认为肩负着推动中国文学发展的使命,自然也应该多多发掘新人。
这次文学比赛,就是奔着这个目的办的。参赛不限年龄,但只收从没发表过作品的新人。
也正因为这种理念,当《巴蜀文艺》的主编收到青年作家联谊会的邀请函时,人家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这倒给杂志社的副主编钻了空子。
叫李小棣回去,就是想趁着主编出差,赶紧把赛程定下来。
主编虽有发掘新人的心思,但毕竟上了年纪,审美还停留在一二十年前。按他那套标准找新人,说不定还会把新人的想象力给扼杀掉。
手底下这些人就打算来个先斩后奏,把大赛的基本框架定好,到时候跟主编汇报,就说是大伙一块商量的,兴许他也不会大改。
把这些事联系起来,李小棣那句“占着茅坑不屙屎”,指的是谁就有点意思了。
李小棣还神神秘秘地跟杨百川透露,这次大赛是和几个国家级大刊联合办的,要是得了奖,就有机会在那些杂志上发表。
这话一下子就把杨百川的兴趣勾起来了。
他盼的就是一朝成名,在全国文坛打响名号。虽说眼下只在厂报发表过一篇小说,但他已急不可耐,不想再在省市级的刊物上打转。
与其说他是个急功近利的人,不如说他对自己的本事有底气,毕竟他脑壳里装着的,是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文学经典。
他打定主意,要把那篇《雾镇》好生地打磨打磨,投到这次比赛里。
白天,大伙都去作协开改稿会了。招待所的走廊上晾着几件衬衫,在风里晃荡,就剩他守着整栋空楼。
他总爱缩在园圃边的条椅上写小说,或坐或趴,反正也没行人路过。树荫底下阴浸浸的,风过时能闻见花草的香气。
这样,他就能最大限度地放肆自己的天性,获得源源不断的灵感。
夜里写不成,李小棣的鼾声像QQ牧场,根本没法安心创作。
即便这样,到第五天时,他还是把初稿写出来了。
那天李小棣开完会回来,把挎包往床头一甩,拽着杨百川下馆子。
走到华福巷拐角,突然拿胳膊肘捅了捅杨百川:“诶,杨哥,今天《渝州文艺》的余主编还问到你嘞!”
杨百川一愣,指着自己:“我?”
李小棣点头:“他问你是不是被打击到了,改稿会都不来参加。我跟他说,不存在的,人家在招待所闭关修炼!”
杨百川点了点头,心底掠过一阵暖意。余主编这么关心自己,是应该当面感谢他一下。
两人晃到长江路,找到了门卫大爷说的那家猪耳朵面。三两面下肚,杨百川拐进国营商店,买了盒浙江产的茶叶,又挑了个扎着红绸带的红富士礼盒。
回到招待所,杨百川给门卫大爷递了根烟,问清余启东的住处,便和李小棣拎着东西找过去了。
余启东住在专家楼里。
二人到楼下时,天还没完全黑,苏联式的砖房立在暮色里,夕阳斜切过来,像烟雾一样挂在外墙的爬山虎上。
敲开门时,杨百川一眼就看到里面十分宽敞。除了一张双人床外,还配备着沙发、茶几、餐桌和一部春雷牌收音机。
余启东见是杨百川和李小棣,眼睛里淌出笑意,连忙把二人迎进屋内,招呼他们落座。
他捡起茶几上的一包中华,抽出一根叼上,又把烟盒甩回去,笑呵呵地说:“你们随便啊。”
杨百川这才发觉,余启东说的是四川话,听着有点像自贡口音,再想起改稿会上他那标准的普通话,实在难得。
见领导,他向来紧张。此刻也是如此,手心冒汗,坐得板板正正。
李小棣倒自在,拿起根烟就放在鼻子底下闻。
“诶,小杨同志,听小棣说你最近在写新作哇?”
杨百川笑着点头:“在写联谊会的命题作文。”
余启东划燃火柴,另一只手拢着火苗,把烟点上:“你们对这个主题有啥子见解嘞?”
李小棣往前一凑:“那天我们聊过这个问题,杨哥的想法特别独到。”还没等杨百川开口,就把那天的对话,一股脑复述了一遍。
余启东翘着二郎腿,倚在单人沙发的靠背上:“后生可畏啊。小棣,你要多跟小杨同志学习。”
杨百川突然想起,之前张虹说过李小棣的身份。看眼下李小棣这副从容的模样,又听余启东一口一个“小棣”,心里觉得那说法更可信了几分。
“《礼记》里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们办杂志的,更应该经常更新观念,多吸纳新东西,才能长远。”
余启东将烟头搭在指缝里,烟雾缭绕间,穿着灰色缎面睡袍的他很像一个道士,“有些人强调自己有民族自信,却把老祖宗的这句话给搞忘了,固守着老一套,不愿意接受新的东西。”
李小棣比杨百川会来事儿,一个劲儿附和。
余启东突然问:“诶,小杨,你晓得那天在会上批评你小说的都是些啥子人不?”
除了那个咋咋呼呼的婆娘外,杨百川挨个说了他们的名字。
提到张虹时,余启东突然哦了一声:“她是不是那个《马嵬》的作者啊?你们看过那篇小说没得?”
杨百川点了点头。
“你觉得她写得咋样?”
杨百川扭头看了一眼李小棣,又转回脑壳:“实事求是地说,很不错,蛮有感情的。”
余启东欣慰地点了点头:“她之前那样否定你,你还替她说话,是个实在人。我就奇了怪了,能写出这种小说的人,咋个会说出那些话?”
杨百川冷笑一声:“当作家的,哪个不会装?”
余启东朗声笑起来:“你把我们几个,连你自己都骂进去了。不过说得在理,太老实的人编不来故事,当不了好作家。”
忽地又陷入沉思,“不过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是在想,她写小说都敢铤而走险、打破陈规,为啥子却又对你的小说提些老掉牙的要求?”
李小棣愤愤地讲:“保不准是想讨好领导!”
余启东觑了他一眼,不置可否:“说起《马嵬》,倒让我想起汪曾祺去年发的《受戒》,好像是发在那个……《燕京文学》上的。你们看过没得?”
李小棣摆了摆头:“我平时看外国文学比较多。”
《受戒》是 1980年发表的,虽说引起了一时轰动,但还没成经典,李小棣没看过也正常。
但杨百川不一样。在后世,这部小说被视为当代文学抛弃前三十年的写法、回归人性本真的先锋,讲这段文学史的老师可没少提。
经余启东这么一说,杨百川还真觉得两篇小说有相似之处。
《受戒》借小和尚明海出家、受戒的经历,串起庵赵庄的风土人情和少年懵懂的情感。
打破了传统佛教题材的严肃感,把荸荠庵的和尚写成了有烟火气的普通人。他们种地、杀猪、打牌,甚至允许还俗,展现出世俗化的生活模样。
明海和农家女小英子在日常相处中暗生情愫,摘莲蓬、划小船,透着股天真烂漫的劲儿,受戒仪式成了青春觉醒的象征。
汪曾祺笔下,乡土中国的诗意和人性的本真尽情舒展,满是对自由生命状态的赞美。
张虹的《马嵬》同样写人性,写的是爱情,是那种纯粹得让人心子朴朴跳动的部分。和《受戒》相比,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杨百川忽然想起学当代文学史时,了解过 80年代关于人性和文学的那场大讨论。这一瞬间,他真切感受到,自己正站在文学的浪潮中,无数个浪头从身边掠过。
80年代的中国文学界,围绕“人性”展开过激烈的争论。
核心问题在于,人性的本质应该怎么理解,文学又该怎么表达。
一边是巴金、钱谷融这些作家和学者。他们重提“文学是人学”的口号,强调人性有超越阶】级的普遍价值,呼吁文学多关注个体情感、尊严和精神困境,反思历史对人性的压抑。
另一边,有些学者坚持阶】级分析的视角,担心“抽象人性论”会掩盖社会矛盾,这其实跟教员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观点一脉相承。
杨百川向来更认可后一种观点。
他记得有学者说过,穷人和富人就像两个不同的物种。富人压榨穷人的时候,哪会想起被踩在脚底板下的也是活生生的人,也是有人性的?他们早就把人性平等给忘记了。
可他也清楚,自己现在还只是个小卡拉米,拗不过时代潮流,还得顺着那些文坛大佬的意思说话。
汪曾祺的《受戒》、阿城的“三王”、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些作品,接连引起热议、大受追捧,除了本身写得好,还因为写到了那些能拍板的人的心坎上。
思绪缠绕间,余启东的一句话忽然撞上杨百川的耳膜:“我想把《马嵬》发在《渝州文艺》上,你们觉得咋个样?”
李小棣赶忙摆手阻拦,将张虹和杨百川的关系,还有她背后使坏的事儿,添油加醋说了一通。
余启东点点头说:“照你这么说,这人做事不地道,那就算了嘛。”
杨百川瞄一眼李小棣,语气犹豫不决:“余老师,我觉得哈……作品是作品,人是人,作品无罪。好的作品就该让大家都看到,不能埋没了。”
余启东愣了愣神,旋即哈哈一笑,身子前倾,一巴掌拍在杨百川肩头上:“我果然没看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