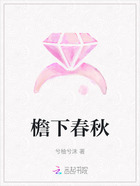
第2章 镜湖碎光
江南的七月在蝉鸣里酿成蜜色的酒。作为生长在黔州群山间的姑娘,我背着褪色的帆布包穿行在青石板巷,帆布鞋底踩着隔夜的雨痕,鞋尖沾着的苔藓绿意里,混着酸梅汤的酸甜与远处飘来的茉莉香。奶奶说过,江南的夏天是块浸了蜜的蒸糕,此刻走在穿堂风里,连汗湿的蓝布裙都染上了几分温柔的黏腻。
攻略里说,江南的灵魂藏在未被商业化的深巷。我避开主街的霓虹,拐进爬满绿萝的窄巷。墙根的石斛花在晨露里舒展花瓣,淡紫色的影子投在砖墙上,像谁用指尖蘸了胭脂轻点。卖糖画的老人坐在竹椅上打盹,铜锅里的糖浆冒着热气,空气里浮动着琥珀色的甜香,勾得舌尖发痒。
手工皮具店的竹帘被穿堂风掀起一角,橱窗里的银杏叶书签在阳光下晃出微光。叶片边缘的枫叶齿痕里嵌着银线,叶脉间的纹路清晰如流水,比机器刻的鲜活许多。我鬼使神差推开门,店主正在擦拭胡桃木货架,见我盯着书签出神,笑着说:“这是古云阁小沈的手艺,他手艺不错,我常让他帮忙做些叶脉雕品。“她取下一片递给我,“姑娘摸摸看,每片叶子都顺着天然纹路刻。“
指尖触到叶脉时,触感粗粝却带着自然的起伏。我买下一片带虫蛀痕迹的书签,店主用素纸包好时,纸包上印着细小的牡丹纹样。巷口的百年银杏在晨露里沙沙作响,我弯腰捡起片落叶,叶脉间的缝隙像极了奶奶未绣完的牡丹——她临终前总说,针线活要顺着纹路走,就像人生要踩着光。手里的纸包带着草木清香,与记忆里的绣绷气息重叠。
三日后,我循着评弹声再次推开古云阁的木门。门环铜铃响起时,穿藏青唐装的老人正在调试戏台追光灯,光斑在他佝偻的背上晃出细碎的金点。二楼临窗的茶盏冒着热气,白菊花瓣浮在水面,杯底沉着片新鲜的银杏叶,叶脉上还凝着水珠。
“姑娘听戏么?头排有座。“老人转身时看见我,眼角皱纹里盛着笑意。戏台上的幕布换了新,《牡丹亭》的牡丹开得正艳,台角的雕花却盖着油布,露出半朵未完成的朱砂蕊。后巷传来断断续续的刻刀声,像某种古老的节拍。
后巷的爬山虎比前日更密了,雨珠顺着叶片滚成珠帘,在青石板上敲出细小的圆斑。沈砚之蹲在墙根,指间夹着刻刀,正在修补砖缝里的石斛花枝。他穿件洗旧的藏青短打,腕间银镯换成了深棕 Leather手环,听见脚步声,抬头时眼尾微挑,阳光穿过藤蔓的缝隙,在他眉骨的疤痕上织出金色的网。
“买了书签?“他指了指我手里的纸包,刻刀在砖墙上轻轻一磕,“这叶子挑了半个月,虫蛀的位置刚好成势。“他忽然将刻刀递过来,刀柄上还带着体温,“要试试么?顺着虫眼走刀,说不定有惊喜。“刻刀刺破叶片的瞬间,我想起奶奶的绣针,却不小心刻歪了叶缘。他看着那道歪斜的痕迹,忽然用刀尖轻轻挑出个弧度:“你看,这样就成了朵花。“
午后忽然落了太阳雨。我躲在廊下看彩虹,沈砚之抱来条墨绿小毯子,随意搭在石凳上。毯子边缘绣着细密的竹叶纹,看得出是旧物。他退后半步,指尖无意识摩挲着银镯,望向戏台方向:“后巷的爬山虎是我十岁时种的,每年暴雨都能遮点雨。“藤蔓覆盖的墙面上,淡紫色的石斛花在雨里轻轻颤动,花瓣上的水珠像谁不小心碰翻了胭脂盒。
“小时候总在后巷刻叶子,“他掏出速写本,用铅笔迅速勾勒雨幕中的石斛,“爷爷说我手稳,适合修古建。“他翻到某页,上面贴着片泛黄的银杏叶,叶脉间嵌着暗红斑点,“这是用戏台旧漆补的,三百年前的匠人也这么修雕花。“
雨珠顺着飞檐滚成帘幕,将我们与世界隔成静谧的孤岛。沈砚之忽然指着砖缝里的铁丝:“这株石斛去年被暴雨冲歪了,我用修古建的扎带固定,没想到今年竟开花了。“他的语气像在说一段寻常的修缮往事,目光却在我攥着银杏叶的手上停留半秒,“修补这事儿,急不得。“
散场时天已擦黑,镜湖的灯次第亮起,像撒了把碎金子。沈砚之抱着工具箱走在前面,博美犬砚台一颠一颠地跟着,腿上的纱布换成了绣着牡丹的布条。路过手工皮具店,橱窗里的银杏叶书签不知何时换成了枫叶,叶脉间用金粉描着两个小字,却被阴影遮住了一半。
“苏郁,“他忽然停步,声音被荷香浸得低沉,从口袋里摸出个纸包递给我,“这片叶子纹路特别,适合夹书。“掌心的纸包带着体温,我听见自己心跳如鼓,像戏台上的鼓点。
回到民宿拆开纸包,里面是片雕工精致的银杏叶,叶脉间用朱砂描着牡丹,边缘的虫蛀痕迹被巧妙修成枫叶轮廓,嵌着极小的银箔。叶片背面刻着行瘦金体:“苔痕映叶,遇光则明“。末尾的“明“字收笔处有刻刀反复修正的痕迹,像他每次见我时欲言又止的模样。
窗外又落了细雨,打在青瓦上沙沙作响。我将银杏叶夹进《牡丹亭》剧本,书页间掉出片泛黄的糖纸,上面歪歪扭扭画着小熊。糖纸上的折痕里,还夹着片细小的银杏碎屑,像枚微型的书签。
旅行的最后一日,我拖着行李穿过青石板巷,帆布包上的流苏扫过斑驳的砖墙。巷口的百年银杏树下,沈砚之正弯腰捡拾落叶,听见行李箱滚轮声,他直起身拍了拍裤脚的尘土,手里攥着片新鲜的银杏叶。
“要走了?“他的语气像在说今日天气,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叶片边缘。阳光穿过他身后的藤蔓,在他眉骨的疤痕上织出细碎的光斑。我点点头,喉间忽然泛起薄荷糖的清苦——那日在皮具店接过的糖块包装纸还夹在笔记本里。
他将攥着的叶子递给我,叶脉上用细笔描着巷口石斛花的轮廓:“看你总拍那些花,刻了片带纹路的。“叶片边缘还沾着新鲜的金粉,像未干的晨露。我接过时,发现他袖口蹭着点暗红漆料,与戏台上的牡丹蕊颜色相同。
“谢谢。“我将叶子夹进行李箱的笔记本,触到夹层里他送的银杏书签,“古云阁的《牡丹亭》,我会记得。“他嗯了声,忽然指向远处镜湖桥:“雕栏修好了,牡丹纹和你裙摆的针脚很像。“我转身望去,晨光里的桥栏泛着温润的光,雕花线条果然与奶奶教我的刺绣针法相似。
告别来得比暴雨更轻。我背着行李走向巷口,听见身后传来刻刀轻叩砖墙的声音,一下下,像时光的节拍。后视镜湖桥的倒影里,沈砚之的身影已重新蹲在石斛花旁,指尖翻动着新捡的落叶,仿佛方才的对话只是穿堂风掠过的瞬间。
坐上返程的车时,阳光正穿透云层,在掌心的银杏叶上投下叶脉的影子。叶片背面的“遇光则明“四字被照得透亮,金粉在颠簸中轻轻剥落,像极了江南夏日里稍纵即逝的流萤。车窗外的青石板巷渐成细线,唯有沈砚之递叶子时,袖口扬起的雪松气息,还萦绕在帆布包的褶皱里。
我知道,有些相遇本就是镜湖碎光,不必追问归期。就像他刻刀下的虫蛀痕,就像我裙摆的旧针脚,都是时光里恰如其分的存在。当列车驶入黔州的群山,掌心的叶子忽然发出细微的脆响——那是江南的雨,是古云阁的风,是某个疏淡午后。
至于未来,或许会在某片新捡的落叶上,看见相似的纹路。那时我会想起,江南的七月,曾有个穿藏青短打的男生,用刻刀为时光缝补出一片温柔的光。而此刻的离别,不过是两片叶子顺流而下的开始——一片漂向镜湖的波光,一片沉入黔州的群山,各自在岁月里,等待下一次遇光则明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