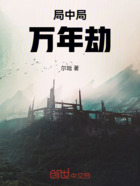
第1章 血色棋盘
我蹲在尸体旁边数地砖。米黄色大理石上蜿蜒的血迹像条扭曲的蛇,在第17块砖的位置分出三滴泪状的血珠——和三天前国贸写字楼的现场一模一样。
“沈顾问,您又在看地砖?”小警察小李的声音带着刚毕业的生涩。他总以为我在故弄玄虚,其实只是习惯用机械性动作保持大脑高速运转。当视网膜自动过滤掉无关信息,那些被常人忽略的细节就会像拼图般自动归位。
死者是位穿着香奈儿套装的女性,左手无名指有长期戴婚戒的痕迹,右手虎口却有握笔的老茧。指甲缝里嵌着极细的碳粉,应该是绘图专用的2B铅笔。我掀开她的袖口,内侧三条平行的淡紫色疤痕,是典型的手术刀划痕——三个月前我在市立医院的停尸房见过同样的伤痕,属于被连环杀手“医师”残害的第三名受害者。
但这次不同。死者颈侧的穿刺伤比前几次深0.3厘米,伤口周围有皮下出血,说明凶手在行凶时曾与死者有过肢体冲突。更重要的是,她右手紧攥着半张撕碎的便签,上面用打印机打出“第19步”三个宋体字。
“通知张队,把近三年所有未破的谋杀案资料送到我办公室。”我扯下乳胶手套,指尖还残留着尸体的体温,“特别注意‘医师’案和去年金融街碎尸案,凶手在模仿前者,但作案手法有刻意修正的痕迹。”
小李欲言又止,喉结滚动了两下:“其实...张队说您上次的侧写报告太激进,不让我们再参考‘医师’案的档案。”
我转身时风衣带起一阵风,扫过墙角那盆枯萎的蝴蝶兰。这栋商务楼的中央空调温度设定在22度,湿度55%,这样的环境下植物至少能存活两周——说明死者遇害前三天,这里的温控系统被人为调整过。
“把监控录像调出来,重点查上周日凌晨到案发前的所有人员出入记录。”我从风衣内袋掏出银制名片盒,递出一张印着“沈昭明犯罪心理顾问”的卡片,“如果张队有意见,让他带着三年前‘医师’案的现场照片来见我。”
走出案发现场时,夕阳正把走廊的玻璃幕墙染成血色。我摸出手机,相册里存着七张现场照片,从第一起案件的第7块地砖,到现在的第17块,数字以每次3的倍数递增。凶手在摆一个局,一个用尸体当棋子的巨大棋盘。
回到工作室时,落地窗外的城市已亮起灯火。我把所有案件资料铺在胡桃木长桌上,用红色图钉在白板上标出七个案发地点。当连线形成北斗七星的形状时,第8颗星的位置正好是市立医院——“医师”最后一次作案的地方。
抽屉里的银色怀表突然发出蜂鸣,这是我设定的每日案情复盘时间。表盖内侧刻着“致最杰出的棋手——M”,那是七年前在国际犯罪心理学会上,某位神秘同行送我的礼物。当时我刚破解伦敦地铁连环爆炸案,而他留下的谜题至今未解。
电脑屏幕突然弹出新邮件,匿名发件人附了段17秒的视频。画面里是双戴着手套的手,正在棋盘上移动一枚染血的棋子。镜头拉近时,我看见棋盘右下角刻着极小的字母“SZM”——是我名字的缩写。
怀表的指针指向23点整,第七次蜂鸣响起时,手机震动起来。来电显示是陌生号码,接通后传来电流杂音,紧接着是重物倒地的闷响,以及一个经过变声处理的男音:“沈顾问,第19步已经走完,下一枚棋子该放在哪里呢?”
我盯着白板上的北斗七星,突然发现每起案件的发生日期,对应的都是当年“医师”案庭审时的证人顺序。当手指划过第七个红点,后颈突然泛起一阵凉意——那是猎物被猎人锁定时的直觉。
“你漏掉了最重要的一步。”我对着话筒轻笑,指尖划过“医师”案档案里证人栏的最后一个名字,“三年前在法庭上,我不仅指出了凶手的作案手法,还记住了他眨眼时的微表情——每次说谎,他的左眼皮会跳动0.3秒。”
电话那头传来急促的呼吸声,随即被切断。我打开加密笔记本,在第47页记下:“模仿者与‘医师’存在直接关联,目标可能是当年参与案件的相关人员。下一步棋,应该会落在证人名单的第8位——市立医院精神科主任陈立伟。”
窗外飘起了细雨,我给自己倒了杯单一麦芽威士忌,冰块撞击杯壁的声音格外清脆。在这个充满谎言的城市里,每个凶手都以为自己是执棋者,却不知从他们犯下第一桩罪开始,就已经成为别人棋盘上的棋子。
而我,既是破局者,也是这盘大棋中最危险的变数。当怀表的指针再次重合,我知道,真正的博弈,才刚刚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