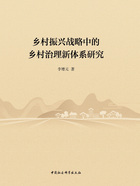
第一章 乡村治理体系的历史变迁
第一节 传统社会官民共治的乡村治理体系
一 代表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县级政府
从历史上来看,县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县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商鞅改封邑制为郡县制的县。商鞅变法后,“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1]。秦统一六国后,郡县制正式确立,县级机构成为中央集权下的一级地方政权组织,是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地方政府机构。郡县制,天下安。郡县制使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有了稳固的政权机构。为加强乡村治理,统治阶级历来十分重视县级机构人员配备与职能设置。在人员配备上,《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县令及其辅佐官是县政府核心人员,不过人员称谓上历代稍有差别,如宋代称县令为县知事,元代称县尹,明清始称知县。县令是县衙中的最高长官,由中央任命,与辅佐官之间存在等级关系。以宋代县级政府为例,县丞、主簿、县尉等是县令的辅佐官。其中,县丞地位仅次于县令,是县令处理县政的重要助手。县令长负责县的全面工作。《后汉书·百官志》注中指出,“令长皆掌治其民,显善劝义,禁奸罚恶,理讼平贼,恤民时务,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县丞助县令长办事,县尉掌管一县甲兵、捕盗之事。以狱政为例,县丞需协助县令处理狱务,《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今仰知县以狱事为重,专任其责,虽与县丞同勘。”并且有“同勘”狱事的权力,在知县“事繁”的情况下县丞亦可以代替主持狱政的前期工作,最终专任其责的还是县令。主簿在地位上低于县丞,承担类似吏人的职能,负责公务文书的上传下达,以及出纳上级拨款。在处理案件尤其是民事纠纷时,主簿也是县令调查事实真相的主要帮手。[2]为更好从事管理工作,在主官与副官之下设有属吏若干,分掌各种事务。秦汉时期这种属官就出现了。
《后汉书·百官志》注引《汉书音义》曰:“正曰掾,副曰属。”县丞助县令长办事,其下还有主吏、令史各曹来分别掌管民政、司法、交通等。[3]之后的属官设置更是呈现出对口设置现象。为更好承担一级地方政府职能,县级政府往往对应中央政府六部设置吏、户、礼、兵、刑、工六房,承担县域教育、考试、治安、征税、户籍管理、财政、工程等各方面事务。另外,县级政府根据需要还设有其他从事具体事务管理的职位。如明代县级政府就有教职、杂职、吏典,其中的杂职就是根据州县的地理、交通、治安、物产等情况设置。根据州县的地理、交通、治安、物产等情况,一些州县还设有一些杂职,诸如巡检司、骤、税课局、库、仓、织染杂造局、河泊所、批验所、递运所、冶铁所、闸、坝等,分别设巡检、骚垂、大使、副使等官进行管理。其官高者为从九品,大多数则为末流。杂职虽然各有所掌,但是要接受所在地州县正官的领导。[4]除此之外,县衙还“辟召”胥吏群体作为辅助管理人员。胥吏是中国古代各级行政衙门中的具体办事人员,是官民的枢纽,主要协助处理狱讼和教育教化、登记人口、编制土地册籍、维持地方秩序、修葺水利工程、调解民间纠纷等工作。《通典》统计,唐中期,官与胥吏共有349863人,而官只有18805人。[5]胥吏虽然没有正式编制,却代表国家来与民沟通,执行各类行政事务。《文献通考》卷35《选举八》引苏轼语:“胥吏行文书,治刑狱、钱谷。”其大意是县官做的关于赋税、盗贼的决策,都由胥吏按职能承担。总体来看,在传统社会,特别是秦统一六国后,县级政府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官方主体,县令(或称知县)、县丞、主簿、县尉,属吏以及其他辅助人员具有正式或非正式官员特征,县级政府设立的各种正式机构或非正式机构具体承担乡村治理各方面事务。
二 联结农户与政府的乡里制度及乡村治理组织结构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有其独特性。一是地缘辽阔,国家与乡村距离远以及“细胞化社会”使国家要实现有效的乡村治理需要大量机构设置,治理成本较高。二是传统乡村社会治理呈现出官民共治的特点。乡里制度是官民共治实践的重要制度形式。所谓“乡里制度”,是封建王朝为汲取乡村社会的人财物资源,维护有序秩序,在县政权之下建立控制农户、地域的控制制度。[6]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在县级政府与百姓之间存在多种类型的乡村社会组织,它们是国家政权向乡村社会的延伸,通过乡里制度各种组织积极参与并协助承担乡村治理职责,呈现出半官方性质。皇权通过这一组织体系对乡村社会保持着不同程度的干预和控制。因此,在传统乡村社会,“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的说法言过其实。
就其基本结构而言,乡里制度由乡、里、邻(无论其具体名称如何)三个县级政权以下层级的地域性管理单元组成,在不同层次的地域性管理单元进行人员设置,实施管理。[7]邻(比、伍、什、保、甲)是最低一级层级。邻是以五家(或十家)民户为基本编组的单元,清人陆世仪(1611—1672)指出:“治一乡,必自五家为比。”邻的核心功能是对民户监控,是国家控制乡村社会的最基础治安单元,邻一般设有邻(比、伍、什、保、甲)长。例如周朝遂设于“野”即国都以外的地区。《周礼》记载,野中“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六遂则设有邻长、里宰、酂长、鄙师、县正、遂大夫等职。两汉在里以下设什伍组织,里有里魁,掌一百户,什和伍各设什长、伍长,并分别主十家、五家,各司其职。北魏孝文帝时实行三长制,形成“党、里、邻”的三级层级,“宜准古,五家立一邻长”。宋代中期实行保甲制,规定,“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8]邻里间相互监督来维护秩序,强化治安。《史记·商君列传》指出:“令民为什伍,亦即或者十家、或者五家,编为一组,互为担保”“相牧司连坐”,唐人司马贞对此解释说,“牧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唐代的邻保组织乃以五家为单位编组而成,其功能以警政治安为主(包括核查户口、纠告逐捕盗贼)以及摊税赋为辅。
里(闾、耆、大保、村寨、社、约、保、甲)以村落和居住地域为基础设置。《说文解字》释闾:闾,侣也,二十五家相群闾也。所谓二十五家组织的里、闾,都是在居住单位的基础上编排建立的。据《管子》所记,齐国之里,有三十家、五十家、百家之别。再如宋开宝七年(974)所置“主盗贼、词讼”之耆长,当即沿用后周制度而来,亦以村落为基础。与邻相比,里最重要的功能是控制户口与田地,以征发赋役。总体来看,“里”实质上是以村落为基础的赋役征收单元。里一般设有里长(闾胥、里魁、里正、大保长),其主要职能是基层治安管理和赋役征发,由村长实际负责各村赋役征纳。《五代会要·租税》载后唐明宗长兴二年(931)六月敕:“委诸道观察使属县,于每村定有力人户充村长。与村人议,有力人户出剩田苗,补贫下不迨顷亩者。肯者即具状征收,有词者即排段检括。”在传统社会,乡是县以下、里以上的地域性单元,非现代意义上的正式政权组织。在乡部的中心聚落设有乡廷,以啬夫或有秩主管乡政。唐代的乡政由所属五里的里正主持,诸乡里正到县衙当值,处理本乡事务,故诸乡不再有乡司驻地,管、都保等相继成为县与里(耆、大保)之间、统领数村的地域行政单元,人口规模从250户到千户不等。明代里甲制下,县直辖各里,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乡级”行政管理层级。到了清代,随着保甲制的全面推行,以千家为基本编制原则的“保”在乡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成为以百家为原则、以村落为基础编排的“甲”(百家)或“里”之上的地域性行政管理单元,并为近代以乡镇为核心的乡村控制体系奠定了基础。[9]保承担着包括查造户口,参与民间词讼,整顿社会治安在内的协助办理地方司法事务和办理各种社会福利事务等职责。依户口以定乡官员成为一些朝代乡里组织员额编制确定的标准。晋制按千户为准,千户以上置史、佐、正三人;千户以下置治书史1人,此外,依户口数(50户以上)另设里吏1人,千户以上置校官掾1人。北齐乡村设党族1人,副党2人,间正2人,邻长10人,共14人。城邑千户以上设里正2人,里吏2人(不常置)、隅老4人。[10]乡里组织领袖人员的选择是乡里制度运行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乡村治理中,乡里制度具有行政性与宗法性两重特性。乡里制度的行政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里组织与王权关系上,传统社会王权对乡村社会有深度的干预和控制能力。封建官僚政治的统治体现着严格的等级秩序,乡里组织是这个庞大权力“金字塔”下的基层组织。乡里组织是统治政权向基层社会的延伸,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获取统治资源的重要工具。清康熙时巡抚赵申乔曾做过如下描绘:“凡害民秕政,不止一端,而惟横征私派之弊其祸尤烈,如收解钱粮,私加羡余、火耗、解费杂徭,每浮额数,以致公私一切费用皆取给于里民。若日用之米蔬供应,新任之器具案衣,衙署之兴修盖造,宴会之席面酒肴,上司之铺陈供奉,使客之小饭下程,提事之打发差钱,戚友之抽丰供给,节序之贺庆礼仪,衙役之帮贴工食,簿书之纸札心红,水陆之人夫答应,官马之喂养走差,与夫保甲牌籍,刊刷由单,报查灾荒,编审丈量等项,皆有使费陋规,难以更仆枚举”[11]。总之,无事不私派民间,无项不苛敛里甲。二是从不同层级乡里组织运行来看,存在明显的上下级关系。如先秦时“什伍以复于游宗,游宗以复于里尉,里尉以复于州长,州长以计于乡师,乡师以著于士师”[12]。另一方面,乡里制度又体现出较强的宗法性特征。不可否认,王权对于乡里组织具有较强的控制力,但是家族、宗族等民间组织也对其产生重要影响,使乡里制度运行呈现出宗法特征。传统乡村社会聚族而居,乡里保甲等组织与家族、宗族组织存在紧密联系,有的甚至交叉重合,家族直接参与并承担部分乡村管理和服务事务,“明朝隆庆推行乡约,许多宗族趁此制定宗族性乡约,以达到宗族控制乡里组织的目的”[13]。同时,宗族长是乡里组织负责人的重要人选来源,乡里组织也会被宗族所掌控。在传统社会,乡里制度是国家有效治理乡村社会的重要制度形式。乡里制度成为县级政府治理乡村社会的重要制度支撑,同时它又内含着宗族伦理思想。乡里制度兼具行政性与宗法性双重特征,是链接政府与农户、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要纽带。通过乡里制构建的乡村组织体系,在推动传统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表1-1 20世纪前历代乡村管理组织结构[14]

表1-1 20世纪前历代乡村管理组织结构续表

三 血缘基础的宗族组织
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传统社会是血缘关系社会。人类社会产生后,经过最初血脉绵延枝状发展,家庭裂变发展为宗,进而经过不断发展形成了庞杂、严密的宗族体系。宗族组织是传统乡村社会最为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之一。明清祁门善和程氏宗族设有一整套系统而严密的组织用以保证族权的有效行使,宗族设族长,族下各分房设房长,房下的小家庭由家长统管,由此形成一个以族长为首,下分房长、家长、族众各层次的微型的金字塔式的管理组织,尊卑、上下、长幼等级极其严格。[15]族长一般按照辈分、官职、德行、财富相结合来“合族公举”产生,是族权的人格化代表。例如,作为祁门善和程氏宗族族长的程新春就具备着以下才德,包括“孝”“恭”“功德化及宗族、乡里”“教子有方,官宦辈出”“得垦殖之方,辛勤起家,艰苦创业”“正直无私”“深孚众望”“治家有方”,进士出身翰林编修邱濬《明故窦山处士程公墓志铭》对其品德进行称赞。
宗族组织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形式,有财产、祭祀、学堂、会社等。在累世同居的场合,宗族与家庭在某种程度上是复合一致的。[16]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宗族不会干预家庭事务。宗族组织经过长期发展一般会形成一定的组织制度与规范,包括成文和不成文的族训、家训、戒条、族范、宗规、族约,并依靠其组织规范进行管理。同时,禁忌、风俗、惯例、习惯法等非正式制度规范更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农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明清时期的畲族家法族规制度采用道德来教育畲民,具体内容包括尊祖敬宗、重孝悌、慎婚姻、务本、安分、和乡里等方面内容,使之知晓、遵守畲族的道德及规范,并对违反者施以惩罚措施。[17]在组织功能上,小农经济使广大农民以追求安定平稳的生活为目标,宗族作为小农群体凝聚共同体的自组织,也以维护和实现这一目标为指向。贺雪峰认为其可用“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来概括。“守望相助”是指维护所在区域的安全与秩序、相互帮助,疾病相扶就是通过超出家庭力量的扶持应对传统小农经济、农户十分脆弱性。例如长沙檀山陈氏族约就有关爱老幼、实义仓等规定,要求宗族内部人员相亲相爱。[18]这种组织功能是比较普遍的。家长、族众是宗族人员的组成结构,族长处于这一结构的顶端,房长次之,房长分管房内事务和协助族长管理全族。家长是各个家庭的负责人,管理着处于“金字塔”下层的族众。[19]明清祁门善和程氏宗族族长的职责和权力主要有:主持祭祀典礼;主管族产;制定执行族规家法;主持宗族事务;教化或惩罚族众;其他职权,如控制佃仆、主持过继等职责。[20]房长也有明确的职责和职权,是房内公共事务的主要管理者,具体有主持支祠的祠祭,召开本房子弟会议,商讨和决策事宜,管理财务,教育子弟,调解纠纷事件,作为代表参与宗族事务管理等。[21]家长对家庭内部事务进行管理,并参与族内事务商讨。在传统社会,宗族组织是一个庞大的民间自组织体系,以血缘为纽带将大家聚合起来,通过明确的分工,完善的宗族内部规范,有序的秩序体系,对宗族成员进行有序治理,也保护着整个宗族大家庭尽量免受外部侵扰。同时,宗族组织也成为宗族成员与国家政权、其他组织打交道的重要依托载体,在乡村治理中具有重要影响力。
四 士绅及乡村社会中的绅权嵌入
在传统乡村社会权力关系中,以乡绅群体为主体形成的绅权是非常重要的权力之一,是国家行政权力与社会权力衔接的纽带。掌握绅权,拥有地方性权威的主体是士绅阶层。何为士绅,胡庆钧指出,士绅主要是少数知识地主或退隐官吏,具有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与知识水准,并在传统的社会结构里具有声望的人物。[22]张仲礼认为士绅是中国自科举制以来产生的社会阶层,这一身份与学衔、官职、功名有着密切关联。[23]总的来说,士绅是传统乡村社会中具有一定地位、身份的特权阶层,因其地位身份的特殊性进而形成了一定的权力结构,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具有地方权威性。绅权是区域性的,是指其影响力处于一定的地理和物理空间范围内。离开这一区域,其也就不再拥有影响他人的权力,当然区域性有大有小。[24]基于乡村士绅的特殊地位与身份,这部分人员具有鲜明的自身特征。总体来看,士绅的特征概括如下:“首先,他们具有较平均水平多的财产,包括土地及财物。经济实力是他们占有地位的基础。由于他们拥有充足的财富资源,这使得他们摆脱传统小农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节奏,能够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关注区域公共事务。其次,他们丰富的社会关系。主要指他们有些做过官或亲属做官,有着与官员联系、交流的方便渠道。再次,乡村士绅一般都受过较多的教育,通过科举考取功名,是乡村知识权威的代表,能够以知识与文化影响和引领农民。”[25]当然,这些条件有可能同时具备,但具备其中的部分就可能成为士绅。
士绅群体及由此所代表的绅权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首先,绅权与皇权具有一致性,士绅是乡里制度发挥作用的基础。绅士的特殊身份能够与官方进行较为方便的沟通,同时乡绅也是乡村地方性权威,这使得乡绅能够承担官方与民间社会的中介,均衡双方利益。县政府及其所属官员是皇权在地方的直接代表,在地方管理上则需要士绅的参与。地方官到达地方的第一件事通常是会见地方士绅。在一些如修桥、修路、发展教育等地方自治事业,官僚要如愿地发扬这德行,其起点为与绅士分润,照例由绅士担任;救灾、赈饥、衡量土地等非常事务也需绅士带头,负担归之平民,利由官绅合得。两皆欢喜,离任时的万民伞是可以预约的。[26]在乡村治理中,乡里制度虽是官方权力在乡里的延伸,但是乡里组织既没有官方权威,也没有地方权威,因此要想完成上级政府交给的各种任务,必须借助绅权这一地方性权力。由此,绅权逐步嵌入乡村社会,成为乡村治理中的重要权力之一。相关学者通过对华北定县和宝坻档案的研究发现:“在整个19世纪,乡保们一旦‘得罪’了地方实力派,便有被罢免的可能。”[27]可以说,乡绅是乡村的潜在领袖。曾经担任惠、湖知府的刚毅曾依靠乡绅推行保甲而得出经验:“常下乡召集耆老绅民,询其某为正士,择优派充保正。”[28]由乡绅保举保长的做法在现实中较为普遍。在公务执行中,保长也离不开乡绅的支持。在一份档案中,保长禀告:“每遇杂差及春秋承催租粮,俱由各庄富绅垫办。”[29]
绅权是社区性权威,乡绅是宗族、社区公共事务的组织者及其代表,是宗族矛盾冲突的缓冲器。乡绅拥有知识、能力、财富等方面优势,与宗族内主要权威成员具有相似性,因此乡绅在宗族治理中拥有极大影响力。另外,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往往存在多个宗族势力,现实中这些宗族之间也存在利益冲突,特别是涉及土地、祠堂等。由于绅权较族权有更大范围的权威与影响力,因此能够在宗族发生冲突时起缓冲器作用,为乡村社会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乡绅还是乡村公共事务的组织者。在传统社会,广大农民在生产、生活中存在诸多需求,有些需求已经完全超出了宗族组织能力范畴,又具有地方性特征。乡绅往往积极参与提供社区内公共产品、参与公共事务处理,出资救灾助困、救济扶持,造福乡里。“乡绅作为社区代表与外界进行联络与事务协商。当农村与官府发生矛盾时,士绅能够作为农民代表向官府表达农民意愿。”总的来说,士绅是传统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中不容忽视的一个特殊群体,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