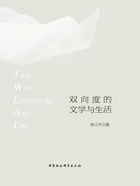
爱在日落后
十多年前,我的师兄,从美国访学归来,站在教学楼光线昏暗的走廊里,跟我们讲“流散文学”,之后这个新鲜词就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回旋。
说到流散文学,我首先想到的是20 世纪俄罗斯侨民文学的三次浪潮。俄罗斯最有个性的文化精英,几乎都因为战争的、政治的各种原因,流亡国外,客居异乡。这样的一拨拨文化巨作,在时过境迁之后,俄罗斯开始接纳它们的回归。而中国流散到海外的华文文学,拥有世界上堪称最庞大的侨民群体背景,却并没有寻到足够壮大的中国大陆读者群。这么多年里,谭恩美、汤亭亭,包括哈金,都已经成了耳朵里的老茧,我也没有兴趣去关注。
然后,大概是机缘来了。
那天在书海里看到《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我知道,我要读它了。它与我命定的缘份就在这一刻到来。就像书中的映映一样,见到那个猥琐地喊着“开瓜”的男人,竟然会有一种预感,知道自己将要嫁给他。映映用心灵的眼睛看到一切危象。当然,我与《喜福会》的最终相会,终究还是一种幸运。
结束了在这本书中的徜徉,有各种情绪袭来。结构与视角精巧、考究,毫无疑问小说在技术上是高超的;而旧习俗旧宅院、新世界新生活的两重天的场景切换,又令情感的暗流在其间汩汩流淌,故事的火焰或明或灭,小说在人物心绪逻辑的设计上,又同时是高明的。
作家谭恩美(Amy Tan)的母语是American English。我读到的这版,是同样身为作家的程乃珊的译本。英汉两相对照,可以看出,译文实在是做了很大程度的补充与加工。英文是很简洁的,程译本把很多的言外之意及未必是作家原意的话,都实现了无痕添加。我倒是认为,如果能采用译者注的形式会更好一些。当然,单就程译的文字来说,是很精妙的,遣词造句非常收敛、冷静,极尽推敲,是我喜欢的风格,但却是一部不忠诚的译著。尤其是还有些漏译的地方,还有些“意到笔不到”译不出来的地方。但这些并不可苛责,何况,作为一个作家,程乃珊应当是把原文作为了再创作的素材,遇到“冰山风格”的句处,她就会忍耐不住要自行铺陈延展。这一种“归化”的译法,英译二传手林琴南,早已经作为先驱在特殊的时代成功地实践过了。
程译最大的不足,是无法准确传达原著不同叙述者的不同言语风格。Suyuan(应当译成“夙愿”,程译本译为“素云”)的叙述中,夹杂了很多罗马化音标编码的汉语拼音,那种英文生涩词不达意,或者说出于文化的隔膜,更愿意使用母语畅快表达的感觉,在追求语言风格流畅的程译本中,是几乎感觉不到的。在19世纪俄国小说的汉译本中,法语单词都是要用特别的字体标注的,或者至少也要页下注。很遗憾文风具有特殊力度之美的程译本有这样一个瑕疵。好在如今的年代,在获取资料方面,太过便捷,我们有英文本可以参照,原文强迫症患者基本可以放下他们的担忧。更何况,说实话,我更喜欢的,还是中文的畅快表达。英文对于我们来说,不是浸淫其中的母语,是很难品出韵味来的。
一 当中国成为故国
Amy Tan生于美国,她在文字间的叙说,暴露了她作为一个并不典型和纯粹的“香蕉人”的存在。她有着许多对于中国文化的好奇和追索,这一点,甚至我都自愧不如。也是通过她的描述,我方才发现自己对身处的这片土地的感情,又更加深沉了一些。
书的封皮是红黄两色。一对拥抱着的母女,前有龙凤呈祥的经典中式图案,后有旧金山地标建筑金门大桥。
龙凤呈祥,这是一个中文小说基本不会采用的装帧。毛笔勾写的“喜福会”,就被这喜庆的象征所烘托着,几乎像是个牌匾,正如霍元甲的“精武门”,有着相当浓厚的民族色彩。
中译本封面设计得大红大俗,但还是相当不错的。
印象最深的是小说中对大户之家陈设的描写。映映的娘家是无锡的首富。她家“有几十间房子,每间房间都置放着沉重讲究的几案,上面装饰着玉香炉或玉制香烟罐,里面放着英国香烟。”她的家“十分豪华,丝地毯、古董、象牙雕刻等等,应有尽有”。这是一种非常有味道的中国旧式家庭的家居陈设。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映映对于奢侈品见怪不怪。她在遭丈夫背叛遗弃后,经过十年底层生活的蛰伏,遇到了美国男人克利福德·圣克莱尔。对于圣克莱尔殷勤赠送给她的自认稀罕的小玩意儿,映映其实知道它们根本不值钱。这是一种隐喻,美中文化的隐喻。在这种隐晦的描写中,我读出了一个身处中美文化夹缝中的人,对于自己作为美国社会中的少数族裔的身份敏感,以及对于自己文化之根的自尊感。这样的一种描写,在阿富汗裔美籍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小说《追风筝的人》中同样有过,且同样令人印象深刻。阿米尔少爷那个堪称是“全喀布尔最美观的建筑”的家,大理石地板、金丝挂毯、水晶吊灯、红木餐桌,各种雅致奢华,汇成一股强硬的底气,即使他后来沦为阿富汗难民,在美国社会里也是一匹瘦死的骆驼。
作为第一代甚至第二代移民,在美国社会中,树立自己故国的浑厚雍容的形象,那等同于在主流人士眼中构建自己的形象。从当年或无奈或期待或愤然地背井离乡,到之后怀念故国文化习俗,对中国的美化,很大程度上是这些海外侨民潜意识里的他乡生存策略。
中国,在母亲们的叙述中,有一种弥漫的贵族气。尽管故事的背景是战争、乱世,但那旧社会的场景里的另一个中国,是如红木家具一般厚重精美的中国。当然,也有妻妾成群、童养媳、重男轻女等等封建制度及观念对女性所造成的压迫和摧残。
对母亲们来说,中国,是一个为她们打下诸多烙印和伤疤同时又盛载着无穷回忆与故事的地方;对女儿们来说,中国只是个概念上的祖籍,是极其陌生的国度——因为发音的相似,她们甚至连太原和台湾都分不清楚。她们甚至连自己中文名的寓意是什么都不甚了了。直到母亲去世之后,女儿才知道母亲名字(Suyuan)的意思是“长久地持着某种希望”,而她自己的名字“精美”,是“好,纯粹的好,好上加好”,她同母异父的双胞胎姐姐,“春雨”和“春花”,是因为她们“生在春天,春天的雨总要比花先到”。名字含义的揭晓,是一个契机,女儿试图去走近母亲具有诗人气质的心,去关注那片悠远绵长又纷繁的文化,她也终于在中国与她的姐姐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她血液中的中国基因,这时终于开始“沸腾”。
异乡人,反而对根有着更迫切的眷恋。
二 当每个人都能言说
“喜福会”究竟是什么呢?
浅表意义上来讲,只是个麻将会而已——最初为抵抗恐惧后来为对抗寂寞,而成立的一个同乡圈子的聚会。有意思的是,打麻将这种四人格局从牌桌扩展成为小说的结构,小说四个部分,分别是四人各自的叙说,正像一局一局的麻将,大家轮流坐庄。不同的主人公之间,有明争有暗斗,有彼此的不屑,也有互相的配合。而东家则是精美一家,她们永远占据“紫气东来”的位次,由她们开始故事,也由她们结束故事。
这种数字上显然精心的布局,如同《神曲》的三部分,每部分三十三歌,严谨端正的结构本身,就是一种无言的道白。
视角的多重,是更能打动人心的。
当你选择让所有的人都来叙说,这个视角,会是一个极易令读者产生共情心的视角。这一点,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当中,重叙牛虻的故事时,我已经有了很深的体会。罪孽无论何等深重的人,当你选择让他开口讲话时,你都会感觉,谁也不能“蔑视一颗破碎、痛悔的心”;厄普代克续写完《哈姆雷特》前传时,哈姆雷特叔父克劳狄斯的私密情感,和莎翁笔下的那个黑色巨人已出现了相当大的反差;简·瑞斯完成《藻海无边》后,我们对于《简·爱》有了新的审视,对于罗切斯特先生,也不得不另眼再观。
《喜福会》当中的这些人物,当她们开始讲述,你会发现,她们竟都是坚毅的、果敢的。即使她们在脆弱的时候,你也相信,她们不会一直脆弱下去。在写到苦难甚至可以说是灭顶之灾的时候,作家的笔触都是冷静、克制、不动声色的,甚至是轻描淡写的。只是,一笔带过之后,却又有千丝万缕依然在连缀。仿若投了一块小石子在水面上,小石子的分量是轻轻的,它消失了,水波涟漪却还在荡漾。
你没有理由轻视如废人一般躺在床上精神崩溃了的映映,她自己知道,她依然是一只雌老虎,目力几乎能洞察一切;你也没有理由低看在离婚冷战中心力交瘁、抑郁颓唐的露丝,她最终拥抱梦境象征的美好蓝图,字字铿锵地告诉她的丈夫:你反正不能就这样把我从你生活中拎出去这么顺手一丢。
当属下能够发声,精英的优越感可能会丧失很多;当每个人都能言说,中心不再存在,如散点透视的一幅画,观者会注意到每一个局部的细节。在这一刻,我们是强悍而天赋才华的薇弗莱;在那一刻,我们是委曲求全不计回报的露丝;在某一个时刻,我们是冷静旁观的精美;在另一个时刻,我们是违心接受另一套游戏规则的丽娜·圣克莱尔。而她们,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千面的自己。
三 当爱在日落之后,在你已死别数年
小说一开篇,精美的妈妈突然去世了。没觉得精美有多悲恸。这种死亡甚至有了一点加缪的《局外人》的味道。莫尔索(《局外人》)只是说,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似乎是在讲述别人的妈妈。精美也是如此,她坐在妈妈惯常的位子上,平静淡然地观望这一切。然后她才慢慢地发现她的损失。悲恸一点点袭来,最后如潮般涌来。
什么时候,你会最爱一个人,往往是在你最爱的人死别之后的数年。
小说当中写到死亡,落笔都是轻淡得很,但死亡事件的后遗症,却是终于要爆发的。
露丝的弟弟平,死于四岁那年。一家人去海边度假,露丝的责任是看管她的弟弟们,尤其是最小的平。然而,平独自一人向大海走去,在崎岖的礁石丛中小心地挪着步子的时候,露丝并没有制止,她只是相信她的爸爸会代替她看管好平。她看到平走到礁石的边缘,向前跨一步,再跨一步,直到跨进海里去,从此,消失在他们的生活里。
露丝的腿瘫软了,像木头人一样挪不动步子,只是呆呆地看着家人们徒劳地搜寻。甚至,她还能在这种时刻去欣赏落日和灯光在海面上的变幻,完全地不通情理。
但平的离去,一直刻在露丝的心里。她的行将崩溃的婚姻,也令她回想起多年前目睹平的离去,而束手无策任由其发生的无奈与漠然。在危机即临的时候,她总是能够有所察觉,但又完全无能为力。这是命运。
“命运,有一半是出自我们的期望,有一半是出自我们的疏忽。”
“失却你所爱的,你必会更珍惜你所失却的,也必会领悟覆水难收的哲理。”
为什么在很多的危机时刻,我们不去尽上百分百的努力,反而会放手,任由灾难的结果出现?露丝代表了人性中的懦弱与放纵,她的母亲,在Suyuan的眼中,同样是一个没有多少主见的人,但她主张,在命中注定没有希望的地方,仍然要“试一试”,“不管怎么,必须再试一试”。这是一种坚忍。她当年打捞落水的平,可谓是千方百计想尽,最终绝望地放弃,也永远都没有放下。她对上帝失望之后,把《圣经》垫在了残缺的桌脚下,一置二十多年,似乎是已经遗忘,但实际上,那是一种纪念平的方式,死去的平的名字,写在《圣经》的书页中,一尘不染。
夭折的平,一直在家人的心头。从来没有真正离去的弟弟平,在冥冥之中令露丝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的命运。这一次,面对丈夫的欺侮,她选择了不再沉默,不再“疏忽”。她似乎倏然便从低眉顺眼的姿态中站了起来。丈夫要求她从家里搬出去,并貌似大度地拨给她一段寻找新住处的宽限时间,她立刻接下话茬,“我早已找到了住处,就是这里!”
这一次,露丝不再坐看残暴的命运来蹂躏自己。如果在几十年前,她能够牢牢抓住弟弟的手,也许一切都不会发生。这次她不会放手,我认为,她是听到了她殁世多年的弟弟的灵魂的呼唤……
露丝是个弱者,但她的弱并不是真的本质。或者说,这世上并没有彻头彻尾的弱者。你以为的弱者,只是个假象。当隐忍的弱者图谋反抗,她不必歇斯底里,就可以杀你于无形。这一点,在另一位主人公的身上,也有过一次极有力量的挥洒。
那就是琳达。
琳达做了数年受气的小媳妇,逆来顺受,婆家却是变本加厉。琳达一朝醒悟,发现了原来光彩四溢的自己,于是决然动手打碎枷锁,奔向自由的新天地。她答应自己永不忘记自己。然后才有了然后,有了薇弗莱这样一个同样刚强的女儿。
作为母女关系的博物馆,这部小说纷繁琳琅。那又是一个太大的话题。
《喜福会》的开篇,是一根千里鸿毛的飘散。生命的沉重,寄附在这根轻之又轻的羽毛上,代代传承。读过全书,我的思绪,也如这羽毛,在天地间飘飞——为女性的解放,为命运的暴虐,为母女的连心,为不可思议的人与人之间的或冷漠或欺压或攀比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