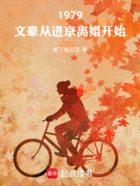
第21章 他们不识货
孙安安点点头,从纸袋里取出一个早已准备好的信封:“都准备好了,就差写上地址。”
陈阳从抽屉里找出一本旧杂志,翻到版权页,指着上面的地址:“就这个,《燕京文艺》编辑部收。”
孙安安认真地抄写地址,一笔一划都写得极为工整。
写完后,她轻轻吹了吹未干的墨水,小心翼翼地将稿子折好放入信封。
“谢谢你,陈阳。”
封好信封后,孙安安真诚地说,“没有你的指导,我可能写不了这么好。”
陈阳摇摇头:“是你自己有才华,我只是提了些建议而已。”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文学创作的心得,直到上课的钟声响起,孙安安才起身告辞。
“我明天去趟邮局,把这封信寄了。希望……希望能有好消息。”
陈阳送她到办公室门口:“一定会的。有消息告诉我。”
孙安安用力点点头,转身走向校门,步伐比来时轻快了许多。
陈阳回到座位,陈阳重新翻开高考复习资料,集中注意力到数学题上。
当陈阳解完最后一道三角函数题目时,窗外的阳光已经西斜,将办公室的墙壁染成了橘红色。
他伸了个懒腰,收拾好书本,回家去了。
路边的田地里,社员们还在弯腰劳作,锄头与泥土碰撞发出沉闷的声响。
陈阳走在乡间小路上,心中盘算着晚饭后要复习的科目。
“哟,这不是咱们的大作家吗?”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
陈阳不用回头也知道是谁——刘项军,那个因为李沐清而一直对他怀恨在心的家伙。
刘项军刚从地里回来,裤腿上沾满了泥点,汗湿的背心贴在身上,散发出一股汗臭味。
陈阳平静地看着他:“有事?”
刘项军酸溜溜道:“装什么装!不就是写了篇破文章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也能写!”
在这个大多数人都要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年代,能够靠笔杆子获得尊重和相对轻松的生活,确实是令人羡慕的。
要说之前的刘项军,单纯羡慕陈阳娶了李沐清,那么现在的刘项军,就羡慕陈阳娶过李沐清和写稿子赚钱了。
“确实没什么了不起的。”陈阳点点头,“所以,能让开吗?我在公社小学坐了一天,肚子饿的不行,要回家吃饭。”
你坐了一天办公室肚子饿,那我在地里干了一天活儿,岂不是要饿死?
刘项军一时语塞,但很快又找到了新的攻击点:“李沐清知道你现在这么出息吗?你们俩该不会没了联系吧?”
陈阳的眼神冷了下来:“我们的事不劳你费心。”
“哈!被我说中了吧?”
刘项军得意地笑了,“李沐清现在在京城吃香喝辣,哪还记得你这个乡下丈夫?她迟早要跟你离婚!”
“她离八回婚,也轮不到你。”
陈阳毒舌一句。
刘项军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心像刀扎一样疼。
打人专打脸,骂人专揭短。
陈阳的这句回答,让刘项军恼羞成怒,拳头不自觉地握紧。
“你神气什么!”
刘项军不服气道,“不就是走了狗屎运写了篇文章吗?我也会写!
我写的《我的生活》已经寄给《燕京文艺》了,到时候你也能在杂志上看到我写的文章!我也去小学教书,也能去一中做报告……”
陈阳挑了挑眉,“你不是投稿了《人民文学》吗?”
“……”
刘项军结结巴巴,尴尬道:“《人民文学》没过稿,他们不识货,《燕京文艺》肯定比他们强多了。”
陈阳无语:“那就祝你成功。”
继续往家走,心情很快平复下来。
路过村口的老槐树时,几个闲聊的老人热情地跟他打招呼。
“阳子,回来啦?听说你去县里讲课了?”
李大爷笑眯眯地问,缺了门牙的嘴说话有些漏风。
那是昨天的事情了,陈阳笑着点点头:“是啊。”
“有出息!”王奶奶竖起大拇指,“咱们村就数你最有文化!”
陈阳谦虚地摆摆手,寒暄几句后继续往家走。
路过供销社时,他想起家里的盐快用完了,便拐进去买了包盐。
营业员是个二十出头的姑娘,认出他后激动得脸都红了,结账时手都在发抖。
“陈、陈老师,”她鼓起勇气说,“我弟弟在县一中上学,他说你讲的作文课特别好!”
陈阳有些意外,温和地笑笑:“谢谢,你弟弟是哪个班的?”
“高三二班,叫张建军。”营业员见陈阳态度亲切,胆子大了些,“他说你讲的那个‘作文像棵树’的比喻特别形象,他一下子就懂了。”
陈阳想起那个在课堂上积极提问的戴眼镜男生,点点头:“他学习很认真,作文底子也不错。”
营业员听了这话,高兴得硬是要少收陈阳两分钱。
陈阳推辞不过,只好道谢收下。
离开供销社,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家家户户的烟囱冒出袅袅炊烟,空气中飘荡着饭菜的香气。
陈阳加快脚步,远远地就看见自家院子里亮着煤油灯的光亮,陈芳正在井边打水,瘦小的身影在灯光下显得格外单薄。
“哥!”陈芳看见陈阳,立刻放下水桶跑过来,“你怎么才回来?娘都热了两遍饭了!”
陈阳揉了揉妹妹的头发:“有点事耽搁了。爹回来了吗?”
“早回来了,正在屋里抽旱烟呢。”陈芳接过陈阳手里的盐,压低声音,“刘项军他娘刚才来串门,说你在路上跟她儿子吵架了?”
陈阳皱了皱眉:“没有吵架,只是碰见说了几句话。”
陈芳撇撇嘴:“我就知道是那家伙胡说八道。他娘可得意了,说什么她儿子也写了文章寄给《燕京文艺》了,以后肯定比你强。”
陈阳失笑:“那就祝他成功吧。”
兄妹俩边说边走进屋。
陈老汉正坐在堂屋的矮凳上抽旱烟,见儿子回来,敲了敲烟袋锅子:“回来啦?吃饭。”
陈母从灶房端出热好的饭菜——一盆土豆炖豆角,一碟咸菜,还有几个杂面馒头。
虽然简单,但热气腾腾,香气扑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