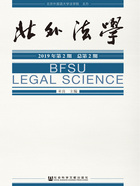
理论和权利研究
内涵、外延及适用:法律意识研究四十年流变考[1]
赵谦 田帅杰[2]
摘要:法律意识即作为主体的人面向法律所生成之一种精神层面的观念形式。依循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开放初期、稳定发展期、高速增长期以及深化改革期这四个阶段的时间线索,所涉法律意识内涵、外延之本体研究以及法律意识与法律制度关系、法律意识培养之适用研究,不断趋向多维度、多样化与多层次的特征,亦达成了一定的体系化研究共识。社会意识诸说即学界以社会意识为研究基点所形成的法律意识特有属性之不同见解,旨在厘清法律意识的内涵。结构要素诸说即学界对法律意识所涉客观事物的结构要素形成之不同认知,旨在识别法律意识的外延。法律制度关联诸说即学界对法律制度与法律意识之间存在何种关系所形成的不同认知,旨在阐释法律意识的适用载体形式。意识培养途径诸说即学界对个性化公民法律意识培养方式、方法所形成的不同认知,旨在列明法律意识的适用方法类型。
关键词:法律意识 社会意识 结构要素 法律制度 意识培养
一 引言
法律意识作为一类指向“特定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主观识别和选择的复杂而综合的社会意识”[3],是作为主体的人面向法律所生成之一种精神层面的观念形式。伴随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对法律意识研究的逐步深入,所开展的法律意识内涵、外延之本体研究以及法律意识与法律制度关系、法律意识培养之适用研究,不断趋向多维度、多样化与多层次的特征,亦达成了一定的“法律意识的基本理论、法律意识现代化理论和当代中国法律意识研究”[4]之体系化法律意识研究共识。基于此,所梳理之法律意识研究命题并非于广义的法与传统、法与道德、法与宗教、法与科学技术等宏大视域下展开,而是仅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关联性更强、指向性更为明确之所涉狭义法律文化话语的具体领域而进行。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伴随后现代法学[5]思潮的兴起,基于对法的非理性、实质性以及非整体性等问题的思考,国内学者对狭义法律文化话语的具体领域所涉法律意识的内涵、外延及适用之研究范畴的认识不断加深。改革开放的相关时间线索大致可厘清为以下四个阶段:其一,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其间对法律意识的研究多引用借鉴外国法律意识研究,仅从心理、社会意识的角度对其进行界定;其二,20世纪90年代至2001年加入WTO的稳定发展期,其间相关研究尝试在法律意识中导入政治性要素,并积极探究法律意识与政治意识的内在关联;其三,2001年至2013年的高速增长期,其间相关研究围绕法律意识的广狭义之分逐步确立;其四,2013年至今的深化改革期,其间伴随公民法律意识的不断提升,相关研究更多地关注在初具规模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施过程中的认知与评价效应。基于此,可尝试依循该时间线索全景式呈现不同阶段的代表性观点并凸显其间的论争,以完成所涉学术史脉络梳理的类型化。最终明晰不同研究范畴在四个阶段的研究主旨,并厘清其内在变迁规律,以探究所涉法律意识研究重心与问题所在而指引未来的研究发展面向。
二 社会意识诸说:法律意识的内涵研究
法律意识的内涵即法律意识“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特有属性”[6],社会意识诸说则是学界以“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与社会存在的总体反映”[7]之社会意识为研究基点所形成的法律意识特有属性之不同见解。可尝试依循四个阶段的时间线索,分别从社会意识理性说、社会意识媒介说、社会意识广狭义说与社会意识主客观认知评价说这四个方面来厘清法律意识的内涵。
(一)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意识理性说”
在这一阶段,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具雏形,西方法学思想理论范式逐步引入。学界开始尝试在引用借鉴的基础上,基于社会意识分析的立场,从作为主体的人对法和法现象之客体法律事实的认知和评价角度来界定法律意识的内涵。例如,“法律意识属于社会意识的一部分,是法和法律现象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8]。“所谓法律意识,是人们对于法(特别是现行法)和有关法律现象的观点、态度的总称。”[9] “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们对法律和有关法律现象的理解、态度和要求的总称。”[10]也有学者认为法律意识是关于“法律现象”[11]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之归属。还有学者认为,法律意识是“对于法律和法律现象”[12]的观点与态度之总称,属于社会文化的内涵范畴。上述观点大体上皆将法律意识的对象限定于“法和法现象”,将范畴限定于“思想(学说)、观点(建议)、心理(情感)与知识”等体现理性的社会意识领域,即形成了一定的共识。
总体而言,相关研究尝试脱离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更多地从法律科学纯粹理性的角度来定义法律意识。虽在一定程度上,以阶级分析法为标签之主流法学分析方法的淡化及流变,助推了所涉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尝试隐于幕后,但仍未彻底舍弃。例如,仍有学者认为“法律意识是一定阶级的法律观点的总和”[13],并更进一步从公民意识角度,探究了法律意识的民主政治之社会实践面向。例如,有学者认为“法律意识与公民意识都属于社会现象范畴,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民主政治之建设与宪法法律之实施间的一致性”[14]。
基于此,学界在更为注重作为主体的人对法律及法律现象的主观态度、观点看法的前提下,尝试梳理了界定法律意识内涵的关键要素:为探索法现象而产生的各种法律学说;对现行法律的评价和解释;人们的法律动机(法律要求);对所涉权利、义务的认识;对法、法律制度相关法律知识了解、掌握、运用的程度;对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这些要素更多地认为法律意识作为社会意识的一部分,同人们的道德观念、政治观念和世界观紧密联系;它也是一类独具特色的社会意识,作为人们就法现象的主观感悟方式,是对法的理性、情感、意志和信念等各种心理要素的有机结合。
(二)稳定发展期的“社会意识媒介说”
这一时期相关研究与前一阶段的研究范式大体上是一致的,所涉社会意识的分析广度和深度略有所拓展,仍然认为法律意识当归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它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是人们对法和法律现象的感觉、认识、期待、评价等法律知识、法制观念、法律观点的统称,反映着人们对法律的看法及守法、执法的自觉程度等等。”[15]但也有学者认为法律意识虽属于社会意识范畴,需将这一概念置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认为“它包括人们对法的本质和功能的看法、对现行法律的要求和态度、对法律适用的评价、对各种法律行为的理解、对自己权利义务的认识等等,是法律观点和法律观念的合称”[16]。这种观点扩展了所涉社会意识分析的广度与深度,进而基于对社会经济基础的认知,而凸显对法和法律制度本质的探寻。
基于此,就前一阶段略有所回避的相关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命题,尝试从民族文化认同和政治制度关联性的角度有所涉及。例如,“法律意识就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社会成员基于民族文化之上的对国家法律体系的主观认知水平、道德自觉性、价值取向以及对该法律体系的支持态度和心理接受能力”[17]。也有学者在认同“法律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体系”之基础上,认为其“与社会的政治制度直接相关”[18],而这种相关性在实践中往往表现为法律意识对政治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石作用。
法作为法律意识的一类客体化、定型化和制度化表征,并非纯粹的法律意识呈现。它往往需依托一定的物质载体,方能更为客观地存续并作用于社会现实。当然法律意识则更多地发挥出社会现实需要与国家立法之间的媒介作用,并体现出一定经济、自然、历史、民族等现实“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本原”[19]支撑的阶级属性。例如,有学者认为政治意识关涉“不同的阶级、政党、集团或个人关于社会政治制度、政治生活、国家、阶级或社会集团及其相互关系等问题”[20],政治意识在社会意识中占据核心地位,并对其他形式的社会意识具有一定指导作用,进而认为“法律意识与政治意识在外延上有较多的交叉现象”[21]。还有学者认为“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现象,具有鲜明的阶级性”[22]。此类观点尝试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方面实现法律意识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有机联结。
(三)高速增长期的“社会意识广狭义说”
这一时期相关研究逐步超出了既有社会意识所涉理性及媒介的分析范式,尝试就其本体范畴命题展开广狭义的界分探讨。就广义说所涉法学理论、知识、心理、情感等范畴而言,认为“广义的法律意识是与道德、文化、经济等意识并存的一种意识形态,主要是法律观念、法律理念、法律素养等综合体系,如‘提高公民整体法律意识’即是此意”[23]。也有学者认为其是对“整个法律现象(特别是现行法)的观点、感觉、态度、信念和思想的总称”[24]。还有学者认为广义的法律意识是法律意识与法律关系在人们头脑中的主观反映,其具有相当的宏观性与抽象性,“它主要包括个人对法律价值的评判机制,个体对自身或他人行为合法与否的评判机制等”[25]。就狭义说所涉法律意识呈现之法现象的形式而言,认为其更多地由“法的形式如何为法的内容服务,法怎样保护与调整各种社会关系”[26]所涉观念表达。此外,狭义的法律意识内含于法律行为全过程,对法律行为的内心机制和主观要件有重大影响,认为其“包括目的、动机、认知能力”[27]。该类法律意识研究在本体范畴上的广狭之分,更多地呈现为宏观性与微观性、抽象性与具体性的差异。
总体而言,无论法律意识的广义界定抑或狭义界定,其作为“社会意识在法律领域中的特殊表现与类型,即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意识形式”[28]是得到广泛认同的。当然在具体范畴上也应涵盖“关于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29]等要素,其心理形式亦具体表现为“人们对法律现象的感觉、知觉等直观的感性心理反应以及法律意见、法律观点、法律思想或者法律理论等理性的心理反应”[30]。对这些要素的解析是厘清法律意识本质内涵的必然要求。
(四)深化改革期的“社会意识主观认知评价说”
这一时期相关研究在沿袭前期研究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尝试从人们对现行法的主观反映角度来扩张法律意识的内涵面向。例如,有学者认为法律意识是人们对“法或法治的一种主观反映和理性认知,是社会主体在思想意识中对法以及法治所形成的稳定的、长久的和潜在的观念”[31],具体可分为“较低级的感性认识阶段的法律心理和高级的理性认识阶段的法律思想体系两个层次”[32]。此外,还有学者对法律意识的内涵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更为广泛的拓展,认为“法律意识是社会主体对法律规范、法律关系、法律行为以及立法、执法、司法等法律现象的一种主观认识形式,是社会主体关于法律的知识、情感、评价与行为倾向的一种综合反映”[33]。这类凸显互动化主观表达的法律意识定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伴随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推进,公民法律意识不断提高的同时,公民主动参与法治建设及相应认知评价活动的重大现实意义。
三 结构要素诸说:法律意识的外延研究
法律意识的外延即具有法律意识“概念所反映的特有属性的事物”[34],结构要素诸说则是学界对法律意识所涉客观事物的结构要素形成之不同认知。可尝试依循四个阶段的时间线索,分别从多层次多要素之丰富外延说、要素界分外延说、内在结构界分外延说与内外结构互动外延说这四个方面来识别法律意识的外延。
(一)改革开放初期的“多层次多要素之丰富外延说”
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作为一种开创性研究,尝试从结构、阶段、要素等多个方面来解析法律意识的“多层次属性”[35]外延。例如,依循所涉主体将其“分为个体法律意识和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法律意识两个部分”[36]。又如,根据法律意识所涉内容,从心理学角度将其划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对法律的理解。第二,对法律的态度。第三,对法律的要求。”[37]其中,对法律的理解主要表现为对法律本质的见解;对法律的态度主要表征为人们对法律是否赞成的态度;对法律的要求则往往表现为社会主体在形成对法律的自觉认知后,希望借助法律实现愿望的主观心态。再如,从法律意识的形式和内容这两个方面来进行划分,“形式上,法律意识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分类。第一,按法律意识的层次结构,可分为法律心理,法律思想,法律学说。第二,从主体数量看,可分为个人法律意识、群体法律意识和社会法律意识。第三,按法律部门的不同,可分为宪法意识,刑法意识,民法意识,经济法意识等。第四,按法律性质不同,可分为奴隶社会法律意识,封建社会法律意识,资本主义法律意识,社会主义法律意识”[38]。其中,法律意识的层级结构表征了法律意识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历程;法律意识主体数量的不同,造就了个人、群体与社会意识的分化;法律部门的不同,表征为不同部门法的法律意识所体现之法律意识的多元化属性与发展不平衡性;法律性质的划分则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标准,体现了法律意识在不同时代发展水平的差异。
此外,也有学者尝试解析法律意识的多样性结构要素。例如,“概括地说,法律意识包括以下四个要素:(1)法律知识,是关于部门法规条例的具体知识;(2)法律概念,即人们对于法律的所有方面得出的完整的概念;(3)对现行法律的评价和要求,如什么法是好的,什么法是不好的,某项规定是否合理,应该怎样规定等等;(4)对遵守法律规定的态度”[39]。进而探究所涉要素的内在关联,以厘清法律意识的“认知—评价—要求”之互动有机结构。
这一时期学界对法律意识外延的研究较为全面,并在明确所涉多层次、多要素的基础上,实现了对法律意识外延的深入研究。其与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实践对法制建设的迫切需要存在密切联系,且对此后法治社会建设的推进提供了颇具针对性的理论指引。
(二)稳定发展期的“要素界分外延说”
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多基于法律意识的构成要素来进行界分。学界观点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其一,“法律知识和法律评价”[40]所表征的二分说。例如,“从人的认识过程分为感性和理性的角度,法律意识可分为法律心理和法律思想体系”[41]。又如,“法律心理是低级阶段的法律意识,是人们对法律现象认识的感性阶段。它直接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法律生活相联系,是人们对法律现象的表面的、直观的、感性的认识和情绪,是对法律现象的自发的、不系统的反映形式。法律思想体系是高水平的法律意识,是人们对法律现象认识的理性阶段;它表现为系统化、理论化了的法律思想观点和学说,是人们对法律现象的自觉的反映形式,在整个法律意识中处于主导地位”[42]。二分说的观点只是对法律意识外延较为浅层次的界定,伴随社会现实的发展,法律意识的形式日趋丰富,该类观点逐渐难以全部涵括处于法律心理与法律思想体系二者之外的部分内容。
其二,三分说。法律意识三分说则是在二分说的基础上,尝试扩展为“法律心理、法律观念和法律思想体系(或称法律理论)”[43]三个层次的界分,认为法律意识包含“法律认知、法律情感和法律评价三个要素或者法律知识、法制观念和法律观点三个要素”[44]。“将法律意识的构成分为三个因素:“第一,知识因素;第二,心理因素;第三,行为因素。”[45]其将所涉知识因素置于法律学习与法律实践场域中,归结为法律认识、客观的法律思想和观点。所涉心理因素被视为一种心理上的体验,归结为法律感、法律情绪、法律感情、法律态度、法律评价等。所涉行为因素则主要包括社会主体的动机、意向、准备、意愿等。这三种因素实现了对法律意识外延的实质概括,最大限度地扩张了所涉外延结构。还有学者基于法律意识的纵深结构层次来进行界分,认为“它们形成由深层到表层的法律意识的结构体,体现了法律意识逐步定型化、稳定化和理论化的过程”[46],从而实现了对法律意识外延的更深层次剖析。
其三,广延要素说。将法律意识界分为“法律认知、法律评价、法律情感和法律调节或者法律的社会心理、法律的思想理论体系、人们行为模式的设定和行为模式的积淀”[47]等要素。还有学者就法律意识的客体、外延展开了一定的全方位整体梳理。例如,“法律意识所反映的客体内容极其广泛,但就其实际应用的角度而言,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两大方面:一是部门法律意识,二是运作法律意识。这是纵向上和整个法制系统的运作环节相一致所反映出来的法律意识,也就是说法制系统的运作包括了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监督环节,相应也就有立法意识、执法意识、司法意识、守法意识和监督意识,而每一方面又可以展开许多具体丰富的内容。以上两大方面纵横交错,构成了法律意识客体的基本内容”[48]。又如,“根据法律意识的社会政治属性的不同,其外延包括占统治地位的法律意识和不占统治地位的法律意识;根据法律意识认识阶段的不同,其外延包括法律心理和法律思想体系;根据法律意识主体的不同,其外延包括个人法律意识,群体法律意识和社会法律意识;根据法律意识的专业化、普及化程度的不同,其外延包括职业法律意识和群众法律意识;根据法律意识所反映的部门法的不同,其外延包括宪法意识、刑法意识、民法意识、行政法意识等等;根据守法动机的不同,其外延包括内在的观点和外在的观点”[49]。该类观点对于实现法律意识外延的系统化、整全化梳理颇有裨益。
(三)高速增长期的“内在结构界分外延说”
这一时期相关研究在沿袭前期要素分类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就法律意识的内在结构来进行界分。例如,“法律意识的构成要素有:法律观点、法律感觉、法律态度、法律信念、法律思想”[50]。又如,“法律意识的内在结构上同样存在着法律心理与法律意识形式两大层次,这是认识论式分析;其中法律意识形式又可再划分为法律意识形态与其他法律意识形式,这是社会学式分析”[51]。此外,亦有部分学者尝试从不同类型主体结构的角度来界分所涉法律意识的外延,并基于“人民法律意识对法律现象的发展、主体范围、心理结构、法律意识主体的不同社会角色规范、法律意识反映的客体内容或者法律实际应用的角度”[52]等不同面向来进行分类。上述观点尝试从主体、客体、内容等方面来更进一步拓展法律意识外延的结构要义,但所涉具体界分标准的科学性是存疑的,有待展开更进一步的深入论证。
(四)深化改革期的“内外结构互动外延说”
这一时期相关研究尝试对法律意识的内外结构展开综合分析,以厘清法律意识内外结构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就法律意识的外部结构与内部结构进行划分。例如,“第一,法律意识的外部结构理论。第二,法律意识的内部结构理论”[53]。其将所涉外部结构理论界定为法律意识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广泛关系问题,将所涉内部结构理论界定为构成要素内部之间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基于法律意识内外结构的互动性,尝试探究法律意识的纵深结构。例如,有学者通过由表及里、由内而外的方法展开对法律意识内外结构的互动性研究,认为“在内部结构当中主要是从社会法律现象的把握方式的角度出发,纵向结构则是从法律意识的发展阶段角度进行研究。法律意识的纵深结构是由法律心理、法律观念和法律思想体系三部分所构成的”[54]。该类观点既尝试对法律意识的内部与外部结构进行划分,又试图厘清二者之间的互动性。其推动了对法律意识外延结构更为清晰、动态、过程化的全面解析,并为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方向指引。
总体而言,法律意识的性质和功能是由其内部要素和外在法律环境所共同决定的。在对传统意义之法律意识内部结构进行解析的基础上,应同步探究法律意识的外部环境。例如,有学者认为“法律意识是人们对于社会存在的客观法律现象的主观反映”[55]。又如,“在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保障社会自治和个人权利的时代背景下,对当代中国既有的法律意识形态进行创新成为历史必然。某种具有政府、市场、社会三元结构的国家观应该成为未来中国的法律意识形态,公正程序则构成整合的制度基础”[56]。进而,通过对法律意识纵深结构的分析,推动形成法律意识的有机内外互动秩序。
四 法律制度关联诸说:法律意识的适用载体研究
法律制度关联诸说即学界对“体现一个国家民主政治的法律化、制度化”[57]的法律制度与法律意识之间存在何种关系所形成的不同认知。法律意识主要存续于价值维度,法律制度则主要存续于规范维度,两者之间的适用与检视往往成就法秩序运行过程的核心环节。基于此,可尝试依循四个阶段的时间线索,分别从法律意识基础说、意识与制度之本原性论争、法律意识影响说与法律意识实效说这四个方面来阐释法律意识的适用载体形式。
(一)改革开放初期的“法律意识基础说”
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虽然不多,但就法律意识之于法律制度的基础作用乃至重要决定性作用,仍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例如,“尽管法律意识决定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于经济基础的运动规律,但它同其他形式的社会意识一样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不容忽视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主要是通过法制建设这一环节来体现”[58]。基于此,认定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在实施法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正确制定法律的认识论基础,是正确适用法律的重要思想因素,是公民守法的重要思想保证”[59]。该类观点能对当下探究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提供必要的基石支撑。
(二)稳定发展期的“意识与制度之本原性论争”
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围绕法律意识与法律制度谁为本原这一命题,展开了较为激烈的讨论,并产生了以下三种主要学术观点。
其一,法律意识本原说。该类观点认为法律意识是形成法律制度的本原,由认知社会发展中立法的客观需要所致,法的创制过程不可能脱离法律意识的作用。例如,有学者从哲学角度与法律角度出发,认为“不仅法的形成过程需要法律意识的中介,法的实施过程同样离不开法律意识的中介作用”[60]。又如,“法律意识是立法的精神源头。立法者确认和保护什么利益和需求,限制什么需求与主张,往往根据的是自己的法律经验、知识和情感等法律意识因素。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其法律意识的左右”[61]。还有学者基于法律意识与法律制度之间的关联关系,认为“法律意识是法律制度产生的主观意识基础,是法律意识的制度凝结”[62]。基于此,立法作为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的工具,应彰显立法者的明确目的。法律意识的中介作用即在于认知社会发展对立法的客观需要,并推动该类客观需要转化为创制法律的动机。
其二,法律制度本原说。该类观点认为法律制度是法律意识的本原,法律意识的产生其实源自法律制度的实施。例如,“法律意识的本原只能是法律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法律意识势必受到其他社会意识形式,如政治意识、道德、宗教等等的影响从而丰富自己的内容,但从哲学的一性与二性的原理看,法律意识的本原只能是法现象”[63]。亦有学者认为“‘法律意识是法产生的前提’不等同于‘唯意态论’。强调法律制度是根据法律意识建立的,并不否认法律制度归根结底依赖于经济基础,而是表明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上层建筑现象区别于经济基础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它是根据人的意识建立的,法律意识仅仅是社会客观需要与国家立法之间的媒介,而不是法的根源”[64]。基于此,事实上尝试将法作为一个客观上存在的社会现象来探讨它同法律意识之间的相互关系。就产生而言,法在先法律意识在后,故而法律制度的本原不应是法律意识。
其三,法律意识与法律制度相互作用说。该类观点认为法律意识和法律制度是相互作用的,皆不能互为本原,所涉本原仅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例如,有学者基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之物质基础,以及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理论基础,认为“法和法律意识作为社会意识的部分、方面而存在,法是法律意识的‘物化’、‘制度化’,法律意识和法,不存在谁为本原,谁被派生的问题”[65]。此外,亦有类似观点认为“以法为核心的法律现象不能成为法律意识的本原,法律意识的真正本原是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主要是居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66]。基于此,法律意识与法律制度应是一种形而上维度中思想上层建筑与制度规范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法律制度在法律意识指引下建立,并同时影响回馈至法律意识的变迁,两者更多地成就法现象运行过程中的不同面向。
(三)高速增长期的“法律意识影响说”
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更多地围绕法律意识对法律制度的影响而展开。培育法律意识的目的旨在推动形成相对科学的法学概念,进而在其指引下完成相对良善之法律制度的规范创设,以实现对有序公共生活的可靠规则指引。例如,有学者以法律与法律意识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矛盾运动原理为研究基点,认为“法律意识在法的制定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客观需要的认知。二是对法律价值的判断。三是对行为界限的选择。四是法制模式的确定。法律意识对法的作用和影响,存在正作用与副作用之分”[67]。又如,“要实现法治现代化,公民法律意识现代化作为其重要的内在驱动力,从根本上影响着法治现代化的进程”[68]。基于此,立法者的法律意识水平对良恶法律制度的影响尤为明显。“正确的与进步的法律意识对法的制定与实施起促进与保护作用;错误的与落后的法律意识,则对法的制定与实施起破坏作用。”[69]故而在法律制度的建设过程中,要重视对正确法律意识的培养与运用以及对错误法律意识的识别与矫正。
(四)深化改革期的“法律意识实效说”
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伴随“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推进,更多地围绕法律意识的具体制度干预实效命题而展开。法律意识作为沟通法律规范和法律实践的纽带,往往通过公众的具体立法要求、评价及行动而助推法律制度的实践进程。例如,有学者认为,伴随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法治观念不断深入人心,人们越来越关注法律制度的内在品质,即合理性、合法性,进而认为“法律意识作为法律制度的灵魂核心,不仅是法律制度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同时还是法律制度能否有效运作的重要保证”[70]。又如,也有学者认为“公民法律意识是地方法治建设的观念基础和思想支撑,构成地方法治建设的评价尺度和精神支柱,有助于地方法律制度的良性实施、运行和完善以及形成外在良好法律秩序”[71]。“法律意识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心理基础和主观价值认同。”[72]基于此,公众法律意识的科学化与理性化应成为法律制度实效化进程中的不可或缺的思想保障与路径指引,最终在当下的社会转型期法治建设进程中,推动“确立法律至上的法治理念,形成良善立法、严格执法、普遍守法、认真司法的法律意识”[73]。更多地由关注法律制度的体系性与完备性,逐步转向关注法律制度的良善性与实效性。
五 意识培养途径诸说:法律意识的适用方法研究
意识培养途径诸说是学界对“存在很大的差异和不确定性”[74]之个性化公民法律意识培养方式、方法所形成的不同认知。法律意识的适用在方法论上旨在确保所涉各类主体法律认知、评价及要求的实效,并导向其心态、观念乃至理论的逐步深化与创新。基于此,可尝试依循四个阶段的时间线索,分别从法律意识培养奠基论、法律意识培养改善论、法律意识培养个殊论与法律意识培养系统论这四个方面来阐述法律意识的适用方法类型。
(一)改革开放初期的“法律意识培养奠基论”
首先,凸显了法律意识培养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性。例如,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法律意识不能自发形成,只能通过外部的马列主义教育才能形成科学的思想体系。要把人们法律意识的培养与改革现行体制的工作统一起来,从而取得最佳效果,使法制建设在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得到协调发展”[75]。基于此,在推进相应的法律意识教育、提升的长期过程中,重视法学研究及相关宣传教育与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是并行不悖的。
其次,法律意识培养的现状不容乐观,“法律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制建设诸环节的协调性”[76]。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同时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法律教育的协调发展,导致社会民间法律意识相对滞后,而掣肘了法律实效的发挥,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有法不依”的重要肇因。例如,有学者认为近年来伴随法制宣传与法治方略的逐步推进,虽然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培养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但是因为为长期以来封建法律意识尚未清除,过早、过多地抵制和批判了资本主义法律意识,社会主义法律实践又刚刚走上正轨,因此无可讳言,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还是非常淡薄的”[77]。所涉社会民间法律意识往往呈现出形式化与表面化特征,法治观念并未深入人心,“因此自觉守法还远远未成为社会风气。表现在当前改革、开放、搞活中,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层出不穷,屡禁不止。个体经济的经营者违法经营、偷税漏税现象更为普遍”[78]。还有学者认为传授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训练法律技能是当前社会实践中开展法律教育的三种重要目的,而目前我国理论法学在培养法律意识上仍存在较大的弊端,“目前的现状是:法学基本理论课程体系明显陈旧,描述方法偏于简单;法律史学则偏重于告诉人们历史上有过什么观点或制度,对历史上的人类法律实践活动(思维、立法、司法)缺乏有机的、总体的、规律性的描述”[79]。该类法律意识培养状况,对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的阻滞效应较为明显。基于此,则应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培养的途径建设,提升法学教育质量,强化法治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法治观念。
最后,法律意识培养的方法有待改善。虽然在法律意识的宏观培养上,“必须学习法律,宣传法制,研究法学”[80],但在“法制宣传教育中有两种倾向:一是干巴巴讲条文,枯燥、难懂;二是渲染犯罪情节,引起副作用和消极后果”[81]。向全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指明了“普法”的对象、内容、要求以及方法和步骤。具体而言,应“首先,针对我国历史上缺乏法制的传统特点,全面而完整地理解法律的含义。其次,要结合经济体制改革这一过程培养人们的法律意识”[82]。在法律意识培养的相应社会环境方面,“首先要有比较健全的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这是培养法律意识的客观条件。其次,培养法律意识需要创造一个严格守法的客观环境和社会风气,使每个公民逐步树立起用法律来指导和约束自己行动的习惯和信念,自觉遵从经济法规的约束和接受法律的惩罚”[83]。在法律意识培养的具体措施方面,“落实措施一般分为动员准备、组织落实、总结考核三个阶段”[84]。此外,“普法教育不应孤立地进行,应当结合道德教育、人生观教育、政治教育来开展普法教育,从建设精神文明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高度,来认识法制教育的意义,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系统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85]。基于此,必须以科学、合理、体系化的方式来推进法治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法律意识,使每个公民逐步树立起用法律来指导和约束自己的行动的习惯和信念。
(二)稳定发展期的“法律意识培养改善论”
首先,法律意识培养的现状有所改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律意识培养工作虽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但我们也注意到,仍有不少公民面对权利的受损不知所措,致使其权益不能得到法律的救济,这一方面给公民个人带来权利的损失,另一方面也使得国家法律权威受到漠视,直接影响到立法目标和法律实效”[86]。具体到公民法律意识的类型而言,“法律权利意识弱于法律实用意识,表现为:宪法意识弱于部门法律意识;民法、经济法意识弱于刑法意识;诉讼法意识弱于实体法意识”[87]。基于此,应凸显公民法律意识的适用导向,让公民能够借此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国家事务管理,并依法监督公权力机关规范行权。
此外,在我国,传统法律观念与现代法律意识的冲突也较为突出。例如,“重人治轻法治、重义轻利、轻诉避讼、重刑轻民、重官轻民等观念”[88]。“我国现代的法律体系主要是参照西方近现代的法律体系(尤其是欧洲大陆法系)的传统而建立的,相和型的中国式法律文化很难契入相讼型的西方式法律体系之中。”[89]又如,“当代中国公民法制观念淡漠、法律意识相对滞后的原因有社会方面的,亦有历史方面的,其中儒家思想的消极影响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历史原因”[90]。“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法律意识传统的残留以及建国以后‘极左’思潮的影响,当前我国人民的法律意识中还存在着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大潮相冲突的若干因素,产生了我国法治建设过程中法律制度的快速现代化与滞后的法律意识之间的矛盾。”[91]基于此,传统法律观念下既有的社会共识较容易生成对舶来法律体系、理念的心理抵触,则有必要在两者之间探寻平衡、综合之道,而尝试融汇成本土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意识与法治观。
其次,法律意识的培养方法有所改善但所涉效益与效率亟待提升。“提高全民族的法律意识是我们实现现代化和走向法治的重大任务与可靠保证,这已是当今全国人民的共识。然而,从目前我们的法学教育和普法情况看,人们对于法律意识内容结构的理性认识还远远跟不上实践的要求。”[92]例如,“法制宣传教育内容偏颇。这是我国法律生活失调的一个原因”[93]。“在我们的普法工作中,很少向公民阐述法律精神,启发一种抽象化的法律权利意识,更鲜见以传统法文化的介入来深层次地唤起公民对于法制的共鸣,这就造成普法总是停留在面上,结果是高投入低产出,也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影响了普法效率。绝大多数地方的普法方式仍主要限于生硬的灌输,并不从观念层和概念入手去阐释法律的构成、目标及内在价值,这就使公民积极守法的动机难以真正形成,这主要就在于公民缺乏对法的必要认同。”[94]这种僵化、生硬的法律意识培养方法往往流于形式,浪费有限的社会资源。
最后,在法律意识培养理念方面,进一步凸显了法律意识培养具体化、明确化导向的重要性。例如,“法制建设的根本在于教育人,强化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邓小平多次强调,“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95]。又如,“‘四五’普法行将开始。具体说来,‘四五’普法应该努力使普法对象了解和树立法治观念,要让他们知道法律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和社会安定的必要基础和保障”[96]。基于此,不同个体的内生、自觉法律意识乃至信仰应与外在法治实践共生为一类相对自足的有机循环法治进程,“法律意识随着公民在社会生活中对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感知感受而逐步养成,植根在人们心中,统率着人们的法律生活和法律行为”[97]。此外,针对大学生这类特殊群体,应推动其自觉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增强其运用法律意识指引自身行为的能力。“加强大学生法律意识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也便是民主化与法制化的进程。”[98] “要充分认识加强大学生法律意识教育的重要性。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要将法律意识教育纳入大学生素质教育体系之中来作整体规划。”[99]切实提升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对全社会法律意识的提升有着较为明显的标杆和表率作用,应予以重点强化。
(三)高速增长期的“法律意识培养个殊论”
一方面,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对法治社会的形成尤为重要。“第一,当代大学生普遍具有一定的法律意识,能够认同法治观念,并能利用一定的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第二,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大多停留在感性认识、直观表面印象的水平上,法律信仰并不坚定;第三,涉及到社会公众利益时法律意识强,但关系到自身利益时,法律意识差;维权意识强,但方式方法手段等却往往不够合理适当,甚至不符合法律程序;第四,部分大学生法律意识淡薄。”[100]但在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方法上,要重视专业实践与理论教学的平衡,科学的培养方法是确保相应培养质量与效率的关键前提。在实践层面,“要加强法律教育和普法宣传实践环节。比如,建立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以法律专业学生的专业实践探索作为提高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平台。又如,在多方力量的关注下进行大学生犯罪预防工作,提高非法学专业学生的法律意识”[101]。在理论层面,“对法律基础课进行教学改革是高校改进在校生法律意识教育和培养的主要途径,要改变法律基础课仅仅是思想教育和法律知识教育的看法”[102]。“法律意识之养成因此也可以说得上是建构法律秩序的首要环节。”[103]
另一方面,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国家公职人员法律意识培养方面的引领效应尤为凸显。“在司法、执法、守法和护法(即法律监督)中,法律意识的好坏,对法律的正确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起关键性作用。”[104] “一个国家实行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本国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以及国家公职人员,尤其是立法、执法和司法部门公职人员具有适当的、较强的法律意识。”[105] “公民意识的培养、党和政府带头守法、司法公信力的重塑,对于公民法律意识的构建尤为重要。当法律业已成为一种普世性规则并因而约束人们的日常活动时,民众的法律意识水平就会与国家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产生密切的互动。”[106]基于此,在普法宣教实践过程中,应注重强化国家公职人员依法办事的工作习惯,维护政府公信力与司法权威,引领公民养成学法、遵法、守法、用法、护法意识。
(四)深化改革期的“法律意识培养系统论”
当下法律意识培养的广度与深度皆有待更进一步拓展,进而实现从文本到现实的系统化法律意识培养。普法宣教存在“地域之间不平衡性障碍”[107]的同时,还“需进一步提升普法层次,加强对公民的权利义务教育”[108]。应加大中西部地区、老少边穷地区普法宣教的力度,努力确立公民的基础法律意识;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针对必要法律常识基本普及的公民,更进一步加强其权利义务教育,着力提升其法律意识认知的水平,以强化其必要的权义行为能力与自觉守法意识。“每个公民遵守法律的行为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在一定的法律意识的指导下实现的,法律意识水平决定着他们的守法状况。”[109] “转型时期的法治建设不仅仅是法律制度的建立和法律体系的完善,更重要的还是法律意识的培养和法律权威的确立。前者属于制度建设的范畴,后者属于文化建设的范畴。”[110]此外,还应更多地在法治实践中逐步形成公民的必要法治思维与认同感,大幅提升公民的法律认知水平与司法行动能力,“由原来的厌法贱讼转变为主动地诉诸法院,寻求司法机关的保护”[111]。
六 结语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法律意识的内涵、外延及适用研究不断深化。本文就所涉社会意识、结构要素、法律制度关联、意识培养途径之核心要义展开历时性研究,初步完成所涉学术史脉络梳理类型化的同时,亦大体诠释了法律意识研究的多维度、多样化与多层次特征。所确立的体系化法律意识研究共识是:应立基于社会意识,在内外双重结构要素表征下,与法律制度实现交互式过程关联,从而达致个性化、多元化的法律意识培养。基于此,法律意识的未来研究重心当更多地置于“观念中的法”维度下,探究其作为“现实中的法”与“文本中的法”之沟通媒介的实证效用;并与部门法体系完成有效对接,以厘清更具现实指引意义之宪法意识、民法意识、刑法意识等部门法律意识。则如何实现公民法律意识的科学化、系统化培养是法律意识研究的关键问题所在,当更多地由培养方式、方法之投入规模效应研究,逐步转向基于实证分析的培养内容、结果之产出质量效益研究,进而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之本土化法治实践,提供更为坚实可靠的法律文化话语保障。
Connotation,Extension and Application:the Study of the Rheology of Legal Consciousness in the Past Forty Years
Zhao Qian Tian Shuaijie
Abstract:Legal consciousness is a kind of spiritual form of concept generated by the human face law as the subject.Following the time clues of the four stages of reforming the starting period,stable development period,high-speed growth period and deepening the reform period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ont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legal consciousnes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gal consciousness and legal system,and the application of legal consciousness training research has continuously turned to multi-dimensional,diversified and multi-level features,and has reached a certain systematic research consensus.The social consciousness is the different views of the unique attributes of legal consciousness form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 with the social consciousness as the research basis to clarify the connotation of legal consciousness.The structural elements are the different cognition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structural elements of the objective things involved in legal consciousness to identify the extension of legal consciousness.The related theories of the legal system are the different cognitions form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gal system and the legal consciousness to explain the applicable carrier form of legal consciousness.The consciousness training approach is the different cognition form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s on the training ways and methods of individualized citizen legal consciousness to list the types of methods of law awareness.
Keywords:legal consciousness; social consciousness; structural element; legal system; consciousness training
[1]本文为2019年度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5批面上资助项目“法治思维引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改革研究”(资助编号:2019M653329)、2017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项目“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法律保障研究”的研究成果。
[2]赵谦,法学博士,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田帅杰,西南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3]贾应生:《论法律意识》,《人大研究》1997年第9期。
[4]刘旺洪:《法律意识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0。
[5]参见朱景文主编《当代西方后现代法学》,法律出版社,2002;高中《后现代法学思潮》,法律出版社,2005;李栗燕《后现代法学思潮评析》,气象出版社,2010。
[6]金岳霖主编《形式逻辑》,人民出版社,2006,第22页。
[7]参见唐昊《当代中国社会意识结构及特点分析》,《兰州学刊》2014年第1期。
[8]董开军:《法律意识对法制协调发展所起的作用》,《法学》1984年第12期。
[9]何为民:《法制宣传教育中的若干心理学问题》,《法学研究》1987年第2期。
[10]王勇飞、王常松:《法律意识结构层次浅析》,《现代法学》1987年第2期。
[11]张洪凌:《从信息控制的角度看法律意识的一般属性》,《法学评论》1987年第2期。
[12]郭建:《当代社会民间法律意识试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
[13]胡开谋、阿木兰:《法律意识与贯彻执行〈经济合同法〉》,《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
[14]谢邦宇:《公民意识·民主意识·法律意识》,《政治与法律》1987年第5期。
[15]刘农:《法律意识淡薄: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亟待攻克的难关》,《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16]赵震江、付子堂:《现代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40页。
[17]贾应生:《论法律意识》,《人大研究》1997年第9期。
[18]刘旺洪:《依法治国与公民法律观念》,《法学家》1998年第5期。
[19]朱景文、李正斌:《法律意识的概念与本原辨析》,《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20]朱景文、李正斌:《法律意识的概念与本原辨析》,《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21]朱景文、李正斌:《法律意识的概念与本原辨析》,《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22]李资远:《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与大学生法律意识教育》,《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23]张正德、付子堂主编《法理学》,重庆大学出版社,2003,第356页。
[24]舒国滢主编《法理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42页。
[25]张正德、付子堂主编《法理学》,重庆大学出版社,2003,第356~357页。
[26]李步云、刘士平:《论法与法律意识》,《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
[27]张正德、付子堂主编《法理学》,重庆大学出版社,2003,第357页。
[28]张昌辉:《法律意识形态的概念分析》,《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4期。
[29]庄菁、陈莉:《大学生法律意识现状分析与思考》,《中国青年研究》2007年第8期。
[30]孙春伟:《法律意识形态的价值属性分析》,《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5期。
[31]于丽芬、戴艳军:《“规范法律意识”中国话语体系的自觉性建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1期。
[32]葛敏:《在校大学生法律意识调查研究》,《前沿》2013年第2期。
[33]秦强:《转型中国的法律意识变迁》,《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34]金岳霖主编《形式逻辑》,人民出版社,2006,第13页。
[35]王勇飞、王常松:《法律意识结构层次浅析》,《现代法学》1987年第2期。
[36]何为民:《法制宣传教育中的若干心理学问题》,《法学研究》1987年第2期。
[37]王勇飞、王常松:《法律意识结构层次浅析》,《现代法学》1987年第2期。
[38]王勇飞、王常松:《法律意识结构层次浅析》,《现代法学》1987年第2期。
[39]张洪凌:《从信息控制的角度看法律意识的一般属性》,《法学评论》1987年第2期。
[40]朱景文、李正斌:《法律意识的概念与本原辨析》,《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41]赵震江、付子堂:《现代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41页。
[42]赵震江、付子堂:《现代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41~42页。
[43]孙育玮:《对法律意识内容结构的再认识》,《学习与探索》1995年第6期。
[44]朱景文、李正斌:《法律意识的概念与本原辨析》,《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45]朱景文、李正斌:《法律意识的概念与本原辨析》,《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46]刘旺洪:《法律意识之结构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7]朱景文、李正斌:《法律意识的概念与本原辨析》,《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48]孙育玮:《对法律意识内容结构的再认识》,《学习与探索》1995年第6期。
[49]朱景文、李正斌:《法律意识的概念与本原辨析》,《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50]舒国滢主编《法理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42~143页。
[51]张昌辉:《法律意识形态的概念分析》,《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4期。
[52]张正德、付子堂主编《法理学》,重庆大学出版社,2003,第357~359页。
[53]赵彦辉:《浅议法律意识》,《人力资源管理》2017年第6期。
[54]高其才:《法理学》(第三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第244~246页。
[55]吴建国、王文华、唐敬业主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5,第115页。
[56]季卫东:《论法律意识形态》,《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
[57]肖扬:《当代法律制度》,《法学家》1999年第6期。
[58]董开军:《法律意识对法制协调发展所起的作用》,《法学》1984年第12期。
[59]康英杰:《论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
[60]朱景文、李正斌:《关于法律意识与法的关系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外法学》1994年第6期。
[61]李蕊、孙玉芝:《公民法律意识——法治之精神力量》,《法学论坛》2000年第2期。
[62]刘旺洪:《法律意识之结构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63]李步云:《法律意识的本原》,《中国法学》1992年第6期。
[64]朱景文、李正斌:《关于法律意识与法的关系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外法学》1994年第6期。
[65]万斌编《法理学》,浙江大学出版社,1988,第172页。
[66]朱景文、李正斌:《法律意识的概念与本原辨析》,《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67]李步云、刘士平:《论法与法律意识》,《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
[68]王爱兰:《试论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内在与外在标准》,《北方论丛》2007年第2期。
[69]李步云、刘士平:《论法与法律意识》,《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
[70]秦强:《转型中国的法律意识变迁》,《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71]宋慧宇:《公民法律意识在地方法治建设中的功能及提升途径研究》,《理论月刊》2015年第1期。
[72]杨燕:《依法治国方略背景下法律意识的功能论析》,《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7年第17期。
[73]秦强:《转型中国的法律意识变迁》,《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74]李步云、刘士平:《论法与法律意识》,《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
[75]董开军:《法律意识对法制协调发展所起的作用》,《法学》1984年第12期。
[76]董开军:《法律意识对法制协调发展所起的作用》,《法学》1984年第12期。
[77]尤俊意:《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律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3期。
[78]郭建:《当代社会民间法律意识试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
[79]赵震江、武树臣:《关于“法律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外法学》1989年第1期。
[80]胡开谋、阿木兰:《法律意识与贯彻执行〈经济合同法〉》,《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
[81]何为民:《法制宣传教育中的若干心理学问题》,《法学研究》1987年第2期。
[82]董开军:《法律意识对法制协调发展所起的作用》,《法学》1984年第12期。
[83]胡开谋、阿木兰:《法律意识与贯彻执行〈经济合同法〉》,《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
[84]康英杰:《论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
[85]何为民:《法制宣传教育中的若干心理学问题》,《法学研究》1987年第2期。
[86]曾坚:《对我国“普法”目标取向的法理学思考》,《当代法学》2001年第7期。
[87]母文华:《当前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现状及成因分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88]郭文才、贺培燕:《传统法律观念与现代法律意识冲突探析》,《阴山学刊》1995年第4期。
[89]贾应生:《论法律意识》,《人大研究》1997年第9期。
[90]李长喜:《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公民的法律意识》,《社会科学家》1997年第6期。
[91]郭艳:《法律价值的冲突与选择——法律意识、道德及现代化》,《宁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92]孙育玮:《对法律意识内容结构的再认识》,《学习与探索》1995年第6期。
[93]母文华:《当前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现状及成因分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94]曾坚:《对我国“普法”目标取向的法理学思考》,《当代法学》2001年第7期。
[9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63页。
[96]王滨起:《法律意识是法治国家进程的基础——兼论“四五”普法的重心任务》,《中国司法》2001年第2期。
[97]李蕊、孙玉芝:《公民法律意识——法治之精神力量》,《法学论坛》2000年第2期。
[98]李资远:《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与大学生法律意识教育》,《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99]李资远:《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与大学生法律意识教育》,《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100]庄菁、陈莉:《大学生法律意识现状分析与思考》,《中国青年研究》2007年第8期。
[101]庄菁、陈莉:《大学生法律意识现状分析与思考》,《中国青年研究》2007年第8期。
[102]庄菁、陈莉:《大学生法律意识现状分析与思考》,《中国青年研究》2007年第8期。
[103]张春燕、张素风、杨丽姣、张兆兴:《高校大学生法律意识养成之客观因素》,《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104]李步云、刘士平:《论法与法律意识》,《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
[105]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221页。
[106]胡玉鸿:《改革开放与民众法律意识的进化》,《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107]焦艳芳:《国家法治现代化与公民法治意识的培育》,《人民论坛》2014年第14期。
[108]焦艳芳:《国家法治现代化与公民法治意识的培育》,《人民论坛》2014年第14期。
[109]高其才:《法理学》(第三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第244~246页。
[110]秦强:《转型中国的法律意识变迁》,《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111]秦强:《转型中国的法律意识变迁》,《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