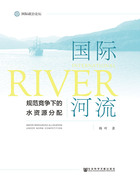
第一节 国际河流水资源分配中的难题
据联合国估计,到21世纪初,全球大约有300起冲突与水有关。[6]根据“水资源小组”(Water Resource Group)的报告,到2030年,全球的水需求量将高于供应量的40倍。这一供需之间的差距因地理位置变化会有所不同,其中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尤为严重。[7]同时,不断增加的淡水需求与有限的供应之间的不平衡,使半干旱与干旱地区的水资源争夺更为激烈。在这些地区,水早已成为稀有商品。20世纪最后30年间,人口增速失控,更加剧了干旱地区对水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研究者视水争议为地区战争的新来源,认为这些地区的水争议是具有零和性质的冲突。21世纪初,在人口与经济快速增长的压力下,由于对水资源控制权的争夺而引发的水危机、水争议、水冲突甚至是水战争成为学术研究的聚焦点与大众媒体传播的热点。根据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评估结果,中东地区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发生水战争的地区。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曾于1977~1991年担任埃及外长一职的布特罗斯·加利一直认为,整个中东、北非地区爆炸性的人口增长及密集的农业模式使日益减少的水存量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会导致武装冲突。因此,加利相信“(中东)地区的下一场战争将会由尼罗河水引发”。[8]除了尼罗河流域外,约旦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也被列为可能引发中东地区“水战争”的两个流域。
一 国际河流水资源的治理实践
从1990年开始,在国际河流的研究与治理实践中,水危机的焦点开始由发展中国家的水资源发展与管理问题,转向于共同水资源日渐匮乏的问题及解决。1977年,联合国水会议在阿根廷召开。大部分与会代表认为:共同水资源的问题应该通过国家之间的谈判解决,谈判应以平等权利与共同协定为基础。[9]1992年,联合国发布《21世纪议程》(Agenda21),其中第18章阐明:跨界水资源及其使用对河岸国家非常重要。以此为基础,这些国家之间的合作值得期待,它们的合作可能与已有的协定或其他相关安排相融合,而这些协定或安排虑及所有相关河岸国家的利益。[10]亚伦·沃尔夫(A.T. Wolf)分析了1874年以来的145个国际水条约,将其收录在阿拉巴马大学的跨界淡水争议数据库之中。沃尔夫认为,国际河流水资源分配是最具冲突性的问题领域,水分配很少在协议中明确清晰地加以规定。从沃尔夫对145个国际水条约中分配的数据来看,条约中涉及平等分配的条约有15个(10%),分配条款复杂但还算清晰的有39个(27%),没有清晰分配内容的有14个(10%),未涉及分配内容或含有可用性分配内容的则有77个(53%)。而在涉及具体水量分配的条约中,分配配额基本上被固定,从而忽视了水文变化以及规模和需求的变化。[11]1997年,联合国第51届会议通过了国际法委员会编撰的《联合国国际河流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草案。然而,这个公约至今尚未生效,对于上述流域的水争议也未提供解决对策。公约尽管建立了避免和解决水资源分配冲突的重要原则,其中包括联合管理和合作责任的原则,但对于水分配几乎没有提供实践性的指导原则。[12]
从沃尔夫建立的跨界淡水资源数据库所反馈的信息中可以发现,在国际河流各流域的治理中,约旦河流域、恒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以及两河流域的水资源分配问题是国际河流治理中展开合作的最大难题。20世纪50年代,上述流域分别开始了相关水资源治理的合作谈判进程。各流域的合作谈判时断时续,谈判形式涉及传统的双边谈判及技术领域的多边谈判。谈判的议题包括:国际河流及其支流流量在流域国家之间的平等分配;水域整合性发展的理性计划;上下游水存储问题、水文数据的收集问题、洪灾控制与管理、水质问题等。从合作谈判进程及结果来看,上述四个流域面临两个共同问题。
第一,各流域内的水资源分配合作谈判过程艰难而又持久,谈判时间大都持续了三四十年。其中,国际河流水资源在流域国家之间的平等分配是最棘手且无果的一个问题。国际河流的分配问题大体上包括两个方面,即水量分配(water itself)与收益分配(benefits from water)。前者与水资源流量或年径流量的配额有关,关系到流域国家对国际河流的水所有权。后者主要涉及共同水资源使用中产生的灌溉、水电及防洪收益,属于水使用权问题。上述国际河流的流域国家都属于发展中国家,位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带,经济形式主要以农业为主。显然,流域国家也意识到,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实现共同的利益。[13]但在实践中,分配问题依然存在众口难调的困境,决定了国家之间的冲突或合作关系,成为上述流域在发展和管理共同水资源中难以逾越的一道障碍。
第二,从合作谈判的结果来看,上述流域的分配谈判在20世纪90年代前很少产生合作成果,且仅限于双边形式的协议或条约。比如在尼罗河流域中,水资源分配合作仅限于埃及与苏丹之间,属于双边合作形式。由于国际河流的覆盖范围最少也是三个国家以上,从理论上讲,分配问题的最终解决形式应该是多边性质。一个没有经过流域内其他国家同意、只在两个国家之间达成的水分配协议,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这样的条约往往会因为排除流域内其他国家的自然权利而遭到不同程度的反对,反对国家通常会因为不是签约国,不受条约约束而采取单边行动,从而使条约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分配问题依然是流域内阻碍合作的关键。因而,在尼罗河这样一个由众多流域国家构成的流域中,双边形式本身就是合作破裂的隐患。也就是说,双边合作必然会排除了流域内其他国家的自然权利。在实践中,又通过强行施加义务于第三方而对其造成伤害,并引发其他国家在流域内的单边行动,更增加了水资源分配问题解决的难度。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述流域水资源分配争议发生变化。其中,恒河流域及约旦河流域内的分配谈判有所突破,流域内的相关国家就水资源分配分别达成协议,迈出了合作的第一步。相反,尼罗河流域及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在分配问题上至今未出现任何合作的迹象。
由此,在分配问题都属于上述流域内水资源争议中的主要问题时,为什么有的流域会形成分配合作,而有的却无法达成合作?在此基础上,本书提出主要研究问题:在什么条件下,国际河流的水资源分配问题会产生合作?
目前,对于国际河流水资源分配问题与合作关系的研究大致从三个方向展开,分别是现实主义的水文霸权合作研究、功能主义的收益合作研究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合作研究。上述研究首先解释了“分配问题阻碍合作”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分别对“在什么条件下,国际河流水资源的分配问题会产生合作”进行了分析研究。
二 国际河流水资源分配难题的现有解释
(一)国际河流水资源的分配结构与霸权下的合作
1.水资源分配冲突的原因:不对称结构
现实主义首先从其基本假设出发,分析水在国家生存和利益实现中的重要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水权争议。从水权争议中产生的水问题(water issue)是一个具有特殊性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水本身的流动性,水流量的不确定性以及易受环境和气候变化影响而产生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这些特殊性进而使那些分享某一河流的分段国家产生对水资源减少与不足的忧虑和紧张,形成冲突或战争发生的心理原因,最终使水资源成为一个国际安全问题。因而,流域国家认为水是一种具有战略特征的资源,事关国家安全,涉及国家的核心利益。约翰·沃特伯里(John Waterbury)在研究尼罗河水文政治时,指出尼罗河的水资源分配实质上就是资源竞争下的权力竞争。也就是说,水资源作为尼罗河流域的战略资源之一,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控制水资源就意味着获得了控制红海入海口的权力。基于这一考虑,流域国家必定会专注于获得此战略资源,获取权力。以米里亚姆·洛维(Miriam R.Lowi)为代表的学者从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出发,认为在国际河流水资源分配中,由于没有可以调解国家间水关系的国际规则和法律体系,流域的水关系同样会受到无政府状态的影响。因此,无政府、权力、安全的假设使现实主义坚信,流域内水关系毫无疑问会呈现出竞争、冲突而非合作的特征。
在上述假设的基础上,现实主义进一步指出,国际河流水资源分配中不对称的河岸结构及权力结构是分配问题阻碍合作形成的具体原因。河岸结构(riparian structure)是指政治单元在地理空间上的位置,比如上游和下游以及权力上的等级结构等。[14]流域内国际边界划定的方式决定了一个国家在流域内是居于上游、中游还是下游的空间位置,同时也影响了流域国家在水权力中的不平衡分配。也就是说,物理地理学在定义河岸国家在水文政治中的相对交易权力中发挥着基本作用。[15]最普遍的观点认为,流域内的上游国家是潜在的最强者,可以控制河流的流量以及改变河流的水质。这种位置不仅使上游国家具有控制下游的天然优势,而且还会使上游国家在共同水域水资源的分配谈判中居于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上下游的结构关系决定了流域内上游国家与下游国家必然是零和性质的水关系。
当然,权力等级结构也可以改变内嵌于河岸结构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等级结构主要建立在军事或经济实力对比的基础上。如果在流域中,一个流域国家在河岸结构上居于有利的空间位置,但处于权力结构中的弱势地位,那么即使是下游国家也会在水资源分配中取得优势。因此,流域内国家之间的权力不对称结构决定了每个流域国家对可获得水资源的控制程度,尼罗河流域即是最好的例证。相较于流域内的上游国家,下游国家埃及具有明显的军事和经济优势,长期处于流域内的权力中心,是流域内水资源使用现状的既得利益者。而上游国家埃塞俄比亚尽管从河岸结构上讲,在流域内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但由于和埃及之间悬殊的实力对比,反而在水资源使用中处于弱势地位。长期以来,尼罗河流域的水资源分配一直处于权力结构而非河岸结构主导下的分配模式,形成流域内水资源使用的不平衡现状。这种不均衡的水资源分配现状最终形成水资源分配现状维护者与改革者之间的矛盾,成为尼罗河流域内水资源争议产生的主要原因。因而,不平衡的河岸结构导致上游国家会通过水资源获得更多权力,而不平衡的权力结构则会使下游国家借助权力获得更多水资源。[16]
2.分配合作:霸权下合作
现实主义从水资源的战略性特征出发,认为上述流域内结构不对称以及实力不对称,使水资源分配中的竞争或冲突在所难免。既然如此,现实主义指出,只有通过霸权下的合作方式,才可能解决水资源分配问题中的争议。也就是说,由流域中实力居优势的国家主导水资源分配进程,建立水文霸权(hydro-hegemony),以阻止竞争或冲突发生。霸权国家会通过其无上的权力优势,有效遏制非霸权国家对秩序的任何暴力性对抗,使非霸权国家遵从霸权国家偏好的秩序。[17]基于此,部分研究者认为,目前中东地区水资源的分配合作需要在霸权的领导下来实现。[18]在中东地区的三大流域中,水权均分别由各自流域中的霸权国家——土耳其、埃及和以色列——所把持,而弱小的河岸国家在水权的获得上基本没有发言权。
马克·吉托恩(Mark Zeitoun)进一步指出,水文霸权只是分配问题产生合作的一个必要条件。[19]分配合作的实现必须基于一种 “领导型”(leadership)关系的积极水文霸权形式,而非“统治型”(domination)关系的消极水文霸权形式。领导型霸权秩序通过权威(authority)而实现,而统治型霸权秩序则依靠强权(coercion)来建立。前者产生非霸权国家合作的机制主要依靠霸权国家说服其他行为体接受其权威,并采用和内化其提供的价值和规范。相对于军事、经济等硬实力,这种能力被吉托恩称为“名誉权力”(reputational power)。简单讲,是在没有运用权力的情况下就会达到预期的效果。[20]领导型霸权形式一般会通过提供国际公共物品,比如秩序、稳定,以加强所有行为体对未来的期望。在国际河流的分配中,水资源使用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收益。因而,领导型的霸权形式可以通过产生遵从的有用性机制(utilitarian mechanism,一般指通过贸易、贿赂、诱惑等形式),应用整合战略(integration strategy),建立收益型合作的动机。比如,建立收益共享的大型水利工程是激发流域国家合作的有效动机。这个过程往往通过提供“搭便车”的条件,减少交易成本,使非霸权国家获得收益。因此,建立领导型的水文霸权是在国际河流水资源分配领域产生合作的充分条件。
3.“霸权主导型分配合作”解释的不足
尽管吉托恩详细分析了实现分配合作的霸权类型,但他本人也认为,尼罗河流域、约旦河流域和两河流域的水文霸权,均属于统治型的霸权形式。霸权国往往采取占有资源的单边行动,借助权力优势将资源分配转向有利于自己的情势,使其成为“既成事实”。[21]约翰·沃特伯里将其称为“事实上的单边主义”,即在缺乏正式的共识下,流域国家擅自进行会影响水资源流量和水质的工程。[22]同时,水文霸权的建立方式主要通过遏制、武力威胁等战略,否认弱小国家的水权,使水资源分配形成不平等的结果。这种行为逻辑非但没有建立“霸权稳定”的支撑点,即水文霸权国家承担适当的河流管理和领导监管责任,弱小的国家通过“搭便车”能获得巨大的收益,从而减少体系内所有成员的交易成本,[23]反而还容易引起流域内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产生反霸权的心理和行动,很难使非霸权国家产生合作动机,霸权秩序呈现出冲突而非稳定的特征。
尼罗河、约旦河以及两河流域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霸权下合作的困境。虽然三大流域的其他河岸国家在水权分配上没有发言权,但是依然对霸权国家的单边行动进行了抵制,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比如尼罗河流域中,上游东非国家的反霸权行动,如坦桑尼亚的尼雷尔宣言、埃塞俄比亚在上游建立的众多小型水库都让埃及头疼不已。两河流域中,流域国家之间不仅没有合作,反而联合反对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工程。同时,叙利亚还使用问题联系的战略,将水资源分配与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相联系,建立了反土耳其水文霸权的战略。结果是,流域内仅仅建立了水文霸权,却并未形成霸权下合作的秩序。那些被视为流域中的霸权国家没有要提供公共物品的意愿,反倒是流域内的小国对建立这样一种机制比较感兴趣,比如尼罗河倡议就是在东非国家的倡导下建立的。这种情况又反过来加强了霸权国的疑心,担心这是小国之间的平衡战略,因而更是在争议中寸步不让。所以,霸权下的分配合作在国际河流分配领域中并未真正实现。
(二)国际河流水资源分配中的收益问题与收益合作
国际关系的另一学派——功能主义学派从共同财产理论及博弈论出发,认为集体行动的难题导致流域国家在国际河流分配问题上很难进行合作。其中三个因素是影响合作的关键变量:(1)产品的类型,例如非再生性资源要比再生性资源的预期收益大得多;(2)河岸国家的数量,一般来说,参与者越多,越难产生合作的结果;(3)河岸国家的同质性或异质性,尤其是能力大小是否对称,偏好或利益是否一致,对问题认知的信念是否趋同。上述这些因素会影响交易成本,决定河岸国家的沟通能力以及做出可信承诺的能力。
1.分配合作:收益共享和收益需求
功能主义学派认为,要想突破上述因素的限制,实现分配合作,关键在于扭转流域国家对分配标准的认知。传统的分配标准是建立在商品基础和权利基础上的分配,这两个标准过于强调物理性的水所有权分配属于零和本质的分配。新的分配标准应以水共享所产生的“收益”为合作基础,流域国家应该更关注通过水资源使用而产生的各种收益,比如政治、经济、社会及环境收益。这将有助于流域国家将水资源分配视为与收益最优化相关的问题,具有正和(positive-sum)性质,促进分配合作的形成。在这种观念下,流域国家会意识到,通过合作获得的收益要大于通过单边行动获得的收益,从而生成合作的动机。
然而,功能主义学派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收益共享并非实现分配合作的充分条件。国际河流的共同财产属性决定了在分配中会存在协调性问题。共同财产具有非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特征,会产生外部性问题和“搭便车”的现象,形成收益协调的问题,导致合作供应不足。[24]协调性问题的核心是相对收益问题,部分学者[25]认为,行为体过多地关注收益分配中“平等”的经济分配标准,从而导致国际河流水资源分配谈判难以达成合作。更甚者,当消费者数目增加时,共同财产的竞争性会加剧,也因此更容易形成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的“公用地悲剧”。最终,水资源分配会产生一个复杂的政策协调谈判过程。相对于绝对收益分配,收益共享产生的相对收益问题更容易阻碍谈判协议的达成。同时,收益共享需要流域国家统一各自收集的水文信息和数据,并量化全部的分配成本和收益。这个要求往往会使相关行为体由于水资源的特殊性而无法估量合作所带来的收益与支付的成本,看不到通过签订协议实现收益共享的希望,所以难以形成合作的意愿。[26]
鉴于此,这部分学者认为,收益需求型合作是实现分配合作的处方。大致来讲,收益需求型合作强调收益分配应以需求不同和大小为标准,避免以平等为原则而产生的“权利”分配困境。沃特伯里列出六个标准来确定需求的不同和大小。大致包括:国际河流流经流域国家的流量与总流量的比例、流域国家分布于流域内整体人口的比例、需由国际河流承担灌溉之可耕地的面积、具有可替代的可用水量。同时,还应考虑维持生命和基本健康的基础性需求,以及保护现存湿地和自然使用权等分配要素。[27]根据这些标准,需将分配建立在经济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上。其中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国际河流的分配中建立一个市场机制,通过市场将水资源分配给那些能产生高经济回报的使用者,以实现国际河流的分配合作。[28]艾榭居尔·基巴罗格鲁(Ayşegül Kibǎroglu)分析了两河流域水匮乏的原因,指出流域国家水匮乏危机是“供求发展”的水管理策略所致。正是由于这种错误的水使用及管理思维,流域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展开了建造蓄水工程的竞争,造成两河流域无效的水使用。为此,作者认为,实现合作的途径是建立地区的水合作机制,流域国家水发展模式应从供应导向转向需求发展。这个过程的首要任务是流域内国家之间的技术性合作先行,其中流域国家间的数据共享是关键。通过共同收集数据的努力,流域国家可能会开始习惯于合作,进而发展促进水资源分配的讨论。[29]当然,在艾榭居尔看来,数据共享的关键是准确地获知各个流域国家确切的水需求量,以此作为实施需求发展战略的重要条件。此外,流域国家还可以借助市场机制,对水进行定价,需求小的流域国家可以以商品的形式,将水资源售于需求大的国家,从而实现在不同需求国家之间的配置,达成共赢。
除此之外,突破收益共享困境的另一条途径是“收益创造”。沃尔夫认为,行为体通过创造联合收益,“做大甜饼”,以转移行为体之间对流量分配的过度关注,从而避免冲突,促进合作。这种方式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美国和加拿大在1961年签订的《哥伦比亚河流条约》(Columbia River Treaty )。在这个条约中,美国向加拿大支付了防洪费用,而同时加拿大也被授予在哥伦比亚与库特耐之间改道的权利,以用于水力发电。[30]近来,地区性合作或倡议逐渐成为实现收益共享合作的主要方案。功能主义学派认为,这个方案可以使流域国家放弃产生冲突的物理性分配,还可以利用地区内现存的制度安排减少制度建设的成本。通过地区合作孕育信任和共同理解,将水问题嵌入在一个更宽广的框架内,比较容易实现合作。目前,致力于拓展收益范围实现地区内合作的观点认为,水资源整合管理(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IWRM)是突破分配困境的最可行的方法。全球水伙伴协会(Global Water Partnership)将其定义为“促进水、土地和相关资源的协作性发展和管理的一个过程,以平等的方式最大化经济和社会福利,同时并未妥协生态体系的可持续性”。[31]IWRM倡导生态可持续规范,出发点是淡水资源是有限且脆弱的体系,因此主张把河流体系作为一个单一的单元进行整体管理,通过整合多维收益,促进流域国家之间的合作。
2.收益分配合作解释的不足
以经济学的方法,根据需求计算收益以突破分配合作的困境,这在国际河流水资源分配的实践中面临很大的挑战。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计算所有可能交易的成本与收益的任务在现实中不仅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且存在很大难度。
在需求大小的界定中,最复杂的问题是流域国家是否在解决问题或合作动机上具有对称性。弗兰克·马蒂(Frank Marty)从行为体的动机结构和利益结构视角出发,认为在国际河流水资源分配制度的形成中存在两种问题结构:集体问题(collective problem)和外部问题(external problem)。集体问题是指共同水域中,各方共同受到同一问题的影响,因此各方在解决这一问题的动机上大致是对称性的,利益是趋同的。而外部问题则是指跨界的水资源问题不是共有的,而是单方的,所以相关行为体在解决问题的动机上处于不对称的结构,利益因此而相异。外部问题要比集体问题复杂,又可分为积极性的外部问题和消极性的外部问题。积极性外部问题是指当外部问题的当事行为体为B时,行为体A为行为体B提供了收益,却没有得到与所提供收益相一致的补偿(国际河流防洪问题属于此类问题)。消极性外部问题是指外部问题的产生由行为体A引发,进而影响了共同水域的另一行为体B,在A向B转嫁成本的同时,并未对这种成本转嫁行为给予相应补偿(国际河流污染问题通常属于这类问题)。在国际河流治理中,相对于集体问题,外部问题是制度建立的更大障碍,会较难解决。如果此问题又和国内的政治社会问题联系起来,那么计算的复杂性极容易再次引发流域内国家对分配中的平等与公正问题的关注。
尼罗河流域水资源的分配实践完全体现了合作动机不对称的问题。流域内,“利益”本身对大多数河岸国家来说,要么是有心无力的梦想,要么是无意识的混沌。这种情况下,以利益为链接的合作无法形成。同时,即使相关行为体对利益分配无异议,依然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比如,通过收益创造的方式有可能会引发牺牲部分国家主权的猜疑。在恒河流域中,尼泊尔水量丰富,但技术优势与经济实力却远逊于印度。尼泊尔通过市场方式向印度出售其部分水资源使用权,这是典型的收益分配需求合作模式。然而,双方之间的合作却由于尼泊尔拒绝印度在其流域内建造水体工程而受阻。在萨拉斯瓦蒂河项目(the Sharda barrage)上,尼泊尔公开表示“从此协议开始,开发(喜马拉雅山)水域的第一步并不是一个联合发展的考虑,而是印度的单独发展。尼泊尔加入到这个共同资源的开发中需要交出自己的国家主权”。[32]这种担心被强大的邻居所控制的情绪蔓延于尼泊尔国内,使尼泊尔的政治家们止步于通过利用其丰富的水资源进行进一步合作的意图。[33]因而,分配问题阻碍合作不只是因为收益的分配问题,而且出于对印度可能会蚕食尼泊尔主权的战略顾虑。
(三)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河流水资源的分配改革
1.分配问题的原因:国内政治经济困境
部分国际河流水资源分配研究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探讨流域内水资源分配的困境。这一研究倾向于认为,在四个流域中,流域内各国均存在国内政治不稳定及经济落后的问题,由此成为水资源分配问题难以产生合作的主要原因。特斯法耶·塔菲斯(Tesfaye Tafesse)指出,尼罗河流域内合作难以形成的部分原因是流域中上游国家国内政治的掣肘。尼罗河流域水关系被嵌入在权力不对称的结构中,相对于实力强大的下游国家——埃及,上游的东非国家实力弱小。因而,这些国家的决策者认为,同埃及展开多边谈判的政治成本太高,缺乏展开多边合作谈判的政治意愿,因而对流域内的合作持冷漠的态度。沃特伯里也认为,尼罗河流域内分配合作受到各国国内政治经济现状的影响。尼罗河流域内大部分国家都存在国内经济不发达和政治不稳定的情况,且经常发生干旱和饥荒,粮食安全政策成为各国长期追求的政策目标。流域内国家将粮食安全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安全利益,从而影响了各国对流域内水资源的认知与行动。沃特伯里具体分析了埃塞俄比亚的水资源政策,并指出粮食安全是埃塞俄比亚的重要国家利益。决策制定者相信,建设大型的水利工程是提高农业生产力最快及具有永久性的解决方法。[34]然而,这种政策思维导致流域各国在流域内的单边行动,从而增加了流域内开展广泛合作的阻力。
约翰内斯(Okbazghi Yohannes)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详细分析了尼罗河流域各国政治经济的整体情况。约翰内斯认为,在尼罗河流域各国中,新自由主义经济规范主导着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战略。新自由主义经济规范主张大规模投资,通过建造规模宏大的大坝以及大型城市建设,以发展国内市场,同时开拓国外市场。[35]在这种经济发展观念的主导下,尼罗河各国通过农业积累来实现农业现代化,以实现粮食安全的战略。农业现代化的主要实现方式之一就是大规模地扩大耕地面积,同时建立大坝引水灌溉。但是,尼罗河各国政府低下的治理效率导致各种大规模的生态危机与资源损耗,非但没有实现消除贫困和实现增长的目标,反而更加恶化了经济危机。同时各国国内普遍存在的社会不稳定所产生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使统治者开始通过内部问题外部化的策略去缓和国内恶化的政治经济局势。[36]于是,尼罗河的水资源成为各国同时关注的焦点,最终产生了针对尼罗河水资源的分配竞争。托马斯·奈夫(Thomas Naff)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中东地区传统的灌溉型农业经济形式,加上恶劣的气候及地理条件,基本上消耗了巨大的水资源。比如在以色列,生活用水仅占1/5,农业用水则占4/5。[37]托尼·艾伦(Tony Allan)更是进一步指出,中东各流域国的国内决策者利用政治言语与策略向国内公众屏蔽水资源现状的信息,伪造关于本国水资源殷实的假象,从而避免合作所产生的政治性投资。[38]
2.实现分配合作:改革、第三方调解及虚拟水
鉴于上述原因,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主张,干旱与半干旱地区的国家,尤其是那些水匮乏的国家应该通过调整水资源的使用方向,从灌溉用水转向国内和工业用水,以重新分配水资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调整国内经济结构、借助外部力量等方式实现流域内的水资源分配合作。
阿伦·埃尔汉斯(Arun P. Elhance)以第三世界国家为案例,深入分析了六个流域中内河岸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对水政策制定以及竞争、冲突与合作结果产生的影响。这六个流域中,粮食安全的困境、宗教与文化分裂所产生的身份与观念冲突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均对各国水政策的立场和战略制定产生了影响,降低了流域内合作的可能性。因此,在阿伦看来,只有通过重建流域国家内部的政治结构、重新调整经济结构才能缓和流域国家在分配问题上的竞争。但是阿伦也认为,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这种可能性都极小,因为这样的重建可能会受到所有流域国家内部保守的经济及政治利益集团、极端的政治集团以及宗教狂热分子的反对。[39]
此外,还有部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主张,上述流域水分配合作难以展开的根本原因是未对此领域进行合理的经济学分析。在上述流域内,农业是水资源的主要消费领域。既然如此,那么水资源是隶属于世界贸易中粮食贸易的一个资源要素。由此断定,流域国家间的水关系应置于地区经济关系框架内,或是国际贸易关系框架中进行分析。在理清这一关系的基础上,这部分研究者提出采取“虚拟水”(virtual water)的政策,以缓解水资源分配争议。“虚拟水”是指通过进口农产品来补偿由于水资源匮乏而造成的农业产量不足的问题。托尼·艾伦建议,既然粮食安全的经济政策目标是产生并激化分配争议的主要原因,那么解决“粮食安全”这个根本问题才是实现分配合作的首要条件。借助“虚拟水”,从外部进口粮食以满足国内粮食需求,可以使这些国家不再因为为解决粮食安全而追求扩大可耕地面积的政策。同时,还应调整流域国家国内的经济结构,重新分配国内各部门用水比例。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农业灌溉用水份额,减少流域内各国在水资源分配中的纷争。
然而,这种方式主要聚焦于水作为农业灌溉的资源价值,而忽视了其在社会情境中所具有的价值作用。[40]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解决方案也只能缓解燃眉之急,且不符合这些地区的实际情况。农业一直是这些地区的主要经济形式,在各流域国家中,80%以上的劳动力均从事农业经济活动。如果实行进口粮食的政策,可想而知,在工业化程度极低甚至是没有的情况下,大范围失业将是这些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产生甚至加剧本来已经存在的政治冲突、经济福利问题及社会不稳定所带来的威胁。同时,“虚拟水”会使这些国家中长期依靠农业牟利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受损,从而遭到其反对,使“虚拟水”政策不具有可行性。此外,“虚拟水”政策还面临着政治安全困境,奈夫就表示,中东国家担心“虚拟水”会对国家安全形成威胁,可能因为某种对国家生存具有重要性的商品而不得不更加依赖外部国家,导致失去刚刚获得的主权和独立。[41]
第三方的干涉与调解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派给出的另一个避免分配合作困境的处方。[42]具体来讲,就是借助流域外具有影响力的组织或国家的技术和资金援助,转移流域内各国对水权的关注,以促进合作。但是阿伦通过对两河流域的分析指出,第三方的干预调解并不能起到以一对百的作用。有影响力的第三方尽管能帮助解决共同水域即时的国际危机,但并不能保证在其斡旋下所达成的协议长期保持有效性。[43]比如两河流域案例中,沙特阿拉伯与苏联曾对叙利亚与伊拉克的塔布瓜大坝争议进行了调解。约旦河流域中,美国也对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水资源分配争议进行了调解,但这些调解基本以失败而告终。印度同意世界银行在印度河水资源分配中的调解与干预,但在恒河水争议中坚决反对任何第三方的参与。
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宏大的方法论指导,国际关系研究也视其为进行科学研究的精神所在。在国际河流水资源分配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国际关系各个学派分别带着本学派的研究纲领,对此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现实主义强调分配问题难以逾越权力竞争的困境,功能主义强调只有从需求基础出发,才能超越各国对平等公正分配水资源的权利纠缠,而国际政治经济学主张从国内政治与经济的视角去审视地区内的水文政治。无论是现实主义的霸权下合作、功能主义的收益合作还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派的合作方案,都回避了“权利”问题在分配合作困境中的存在及作用。也就是说,分配是权力之争也好,收益之争也好,竞争的核心本质上均是“谁应该拥有权利以及拥有多少”。现实主义在强调水权争议的权力结构背景时,忽略了流域国家之间的权力竞争也是各国对水资源“权利”的竞争。功能主义在分析收益矛盾时,也认为横亘在水资源分配中的主要问题是流域国家在坚持“权利”立场上的坚韧性。当然,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分析国内政治经济在流域内水文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时,其实已经开始探讨“权利”问题形成与演化的国内动力。只是这些学派仅把“权利”问题当成了擦边球,一以贯之地徘徊在自己的研究纲领内,坚持纲领内部的研究议程和研究方程式,并赋予问题以熟悉的答案。
事实上,“权利”在水资源分配中已经不再只是“问题”而已,而是形成各种各样的“规范”,嵌入在流域内的水关系中以及流域内各个国家水政策的制定中。“权利”规范表明了各国对如何适当分配共同水资源的不同期望,不同的期望汇聚在一起,进而产生竞争,并成为国际河流水资源分配合作的阻力。由此,本书认为,分配问题的本质是水权争议,分别指一组所有权之间的权利竞争与一组使用权之间的权利竞争,“权利”规范竞争是产生国际河流水资源分配问题的根本原因。
(四)国际河流治理中权利规范的研究现状
国际河流中的“权利”以及“权利”争议的研究一直是国际法的研究议程。[44]国际法主要从权利与义务的角度切入,探讨国际河流水资源的分配及使用中一直有争议的主要“权利”,比如“合理平等使用”“不伤害”“优先使用”等权利原则。研究主要从两条线上展开:第一个研究路径是从法学理论上描述了这些原则形成的历史与发展过程,并从法律规范性的角度分析国家在使用国际河流水资源时是否应享有某种具体的“权利”,以及该承担何种具体的责任。研究核心是分析在什么条件下,权利具有正当性,义务承担具有合理性。比如,首次使用国际河流水资源的国家是否能由此获得 “现存使用”(existing uses)的“权利”,并使接踵而至的使用者不能从法律上进行干涉?第二个研究路径关注具体的问题领域,分析上述原则在各流域的水资源分配条约实践中的应用情况,包括上述“权利”与“义务”的适用范围,这些权利与义务之间的矛盾以及矛盾产生的法理性原因。
国际法对不同“权利”原则之间的争议研究基本上都是从法律文本出发,即从文本的内容中识别原则之间的不相容,以及这种不相容在实践中的反馈。然而,涉及国际河流的国际法一方面本身并不成熟,没有产生稳定的适用范围;另一方面,也无丰富的司法实践来观察“权利”原则之间发生矛盾及发展的过程。因此,目前的研究不能清楚明了地获悉不同“权利”原则之间的矛盾与分配争议及合作的关系。同时,国际法对“权利”研究的理性立场,排除了实践中水与个体及群体等社会行为体的关联性与嵌入性,由此而忽视了这些社会行为体在水政策的论证中对“水”嵌入了何种意义及所具有的不同理解。[45]因此,也无法得知,为什么国际河流相关法律文件中的权利与义务未能在实践中得到遵从。此外,单从法理角度来窥探“权利”之间的竞争如何影响分配问题的合作稍显单薄无力,无从知晓隐藏在这些“权利”原则后面的“黑洞”。因而,国际法的“权利”研究,与只讲“权力”的现实主义及只讲“收益”的制度主义大同小异,至少在遵从理性和价值中立的研究取向方面并无二致。
理性主义假设的研究仅提供了影响行为结果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而无法分析行为变化的内在根源,对解释行为体本质性的、内在目标变化很是乏力。建构主义在解释导致行为者内在本质目标的变化上是有力的,它提供了关于产生此类变化的可变的假设。[46]一些致力于后实证主义方法研究的学者开始呼吁,对国际河流治理的研究应从技术性或经济研究上进行转向,聚焦于治理的政治学动力分析。为此,必须审视规范结构、规范问题等在各类治理中扮演的角色。肯·康克(Ken Conca)认为后实证主义方法拒绝现代研究寻找普遍规律的有用性研究,在世界是复杂和多样的背景下,需要抛弃实证研究对可预期性、简洁与简单化的关注,而更应该聚焦于政治事件和政治过程的独特性。[47]至此,本书认为,从规范的角度来理解国际河流分配中的“权利”,希望看到的不只是上游国家在“绝对主权权利”上表现出来的行为一致性,或是下游国家在维护“历史权利”上的一致立场,而是理解这些“权利”背后分别都嵌入了行为体怎样的价值观和认同。比如马蒂认为,印度与尼泊尔的班杰苏瓦尔项目(the Pancheshwar project),折射出不对称性的动机结构和相异的利益诉求所导致的分配冲突,从而产生制度创设的障碍。但是,马蒂其实没有意识到,这并不是制度难以形成的唯一原因。印度与尼泊尔对“水权”(water right)这一概念及属性存在认识与理解上的差异,这使双方很难形成协作。印度国内对水权的理解是建立在作为“公共财产”(public property)的属性,而非商品属性的基础之上。当尼泊尔把水当作一种商品来与印度交易时,印度人自然难以接受。造成这一理解差异的原因则是隐藏在收益分配冲突后面的规范竞争,是制度形成障碍的深层次原因。因而,水资源分配争议犹如剥洋葱,分配冲突包裹着价值冲突,价值冲突又包裹着规范竞争。究其原因,是每个流域都有一个关于水的“故事”,而每一个流域国家同样也都有各自的水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