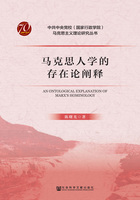
第5章 “存在”论
本章内容摘要:
存在论是哲学大厦之基。作为一种因果还原论,存在论所追寻的是越过“最近之因”的“最后之因”。这一追问形成了哲学史上两个迥异的本体论传统:“实体本体论”和“生成本体论”。实体即本体,自本自因,自根自据,独来独往,自由自在,既无生发也不退场。人类追寻实体的初衷是为了寻找“安身立命之本”,结果却陷入“无家可归之境”。有鉴于此,部分哲学家们高高擎起了“拒斥本体论”的旗帜,以实体本体论哲学之误而否定“本体论追求”的合理性。其实,此乃因噎废食的做法。解决本体论哲学之误的出路不在于告别本体论,而在于以符合现时代需要的策略重建本体论。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哲学家们关闭了传统本体论哲学的大门,但又开辟了现代生成本体论的道路。传统本体论囿于“实体”情结必然导致“存在‘存在者’化”,而现代本体论则是让“存在者‘在’起来”。本体论追问“是”的问题,其意义却超越“是”的领域,任何“是”的追问都指向“应该”,任何本体论都内含价值论的意蕴,缺乏价值维度的本体论是无效的。
人类理性天然具有一种刨根问底、探本溯源的品格,这一追问即本体论[1]的追问。“本体论”乃哲学大厦之基,是哲学的核心领域。“本体论追问”蕴藏了人类自身求真、向善的永恒使命,代表了人类超越当下、走向美好的不懈追寻。有人类史以来即有本体论追问,因而古老;然而本体论追问穿梭于古今而意义常新,因而年轻。本体论追问永远在途中,是一条走不尽的漫漫长路。
第一节 因果与还原
存在论,归根到底是对原因、根据的追问,无论是本原论形态的本体论、本质论形态的本体论,还是生成论形态的本体论,莫不如此。但是,本体论作为追问存在之为存在的学问,它不是追问“存在”的最近原因、最初根据,它所追寻的是越过“最近之因”的“最后之因”,捕捉的是“存在”的最后原因、最终根据。一般来说,事物因果链上的原因均不足以构成事物何以存在的“本体论根据”,真正的“本体”很难在因果链上得到明确直观的反映。比如,追寻人之存在的本体论根据时,我们不能把人成为人的“最近之因”即男女交合的行为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而是要追问人之为人的终极原因。不同哲学派别对人之为人的终极根据的回答是不一样的,宗教神学本体论往往从人之外的神秘世界去寻找人之为人的存在论根据,人之为人的终极原因是上帝的造化,上帝化生万物,化生人。古希腊早期的自然本体论往往从人之外的自然世界去寻找人之为人的奥秘,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某种自然物质或自然实体的存在,人被归结为物质性的自然存在。德谟克利特则提出人的本性是从肉体原子和灵魂原子的结合中产生的,人的灵魂或理性不过是原子的运动形式而已。马克思则从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的结合处破解人的存在之谜,这一存在论认为,人之为人的终极原因在于人类自身的感性活动,人是实践的产物和结果,正是在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中,人方成其为人。生存论本体论认为,“人的现实生活”“人的生命存在”是自己最本原的基础。上述这些都是从本体论的高度来回答人之为人的终极原因。
存在论(本体论)是一种因果还原论,从“多”还原为“一”。哈贝马斯指出:“形而上学试图把万物都追溯到‘一’。自柏拉图以来,形而上学就明确表现为普遍统一的学说;理论针对的是作为万物的源泉和始基的‘一’。”[2]“一”与“多”,既对立又统一,“一”是本源,“多”是派生;“一”是原因,“多”是结果;“一”是主词,“多”是宾词;“一”派生“多”,“多”源于“一”;“一”主宰“多”,“多”服从“一”;任何“多”无非都是“一”的外化、展开和实现,任何“多”都可以化约为“一”,都可以追溯到“一”,都可以还原为“一”。可见,存在论(本体论)是一种还原论,但不是一般的还原论,而是彻底的还原论,还原的是事物背后的最终原因;构成万物存在之根据的最终原因本身并没有更深刻的原因,对最终原因的追问在现实中是无效的,在逻辑上是非法的。存在论(本体论)是对“本原”的追问,但不是一般的追问,而是终极的追问,也就是说追问至此已经完成,“本原”已经呈现,对“本原”本身的追问是非法的、无效的。存在论(本体论)是对“原因”的探寻,但不是最近的原因,而是最后的原因;不是诸多的原因,而是“多”后面的“一”,是某种“唯一者”。
这种因果还原论既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明显的缺憾。还原论将饱满的社会存在向后追溯、分解还原到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层次,将一切丰富性化约为简单性来处理,但是,这样往往导致在分解还原的过程中“要紧的东西都跑了”,[3]从而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西方传统的本体论哲学依凭逻辑建构出来的概念世界,尽管严密规整、合乎逻辑,具有不可挑战的权威性,但相对于灵动的“现实世界”而言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这种把“多”还原为“一”,把具体还原为抽象,以追求最后的绝对本体的还原方法和超验方法,必然会剥夺时间和空间的维度,直接抹掉现实世界的丰富性和历史性,必然远离现实的人,导致对生活世界的粗暴践踏。
第二节 实体与本体
在西方传统人学中,实体即本体,本体也以实体的形式表现出来。康德说:“在世上一切变化中,实体保留着,而只有偶性在变更”。[4]实体自本自因、自根自据,独来独往、自由自在,既无生发也不退场。唯其如此,它才成为世界的最终根源和最后基础,才成为本体。
笛卡尔、斯宾诺莎、黑格尔对“实体”都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其内涵大同小异。笛卡尔认为,“实体”是能自己存在并且其存在不需要任何别的事物的一种东西。斯宾诺莎也认为,实体应该被“理解为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换言之,形成实体的概念,可以无须借助于他物的概念”。[5]黑格尔说:“实体”是“最高尚的、最自由的和最独立的东西。”[6]根据他们的观点,“实体”的存在不需要根据、不需要理由,从时间上来说,它是无限的、永恒的;从空间上来说,它是唯一的、不可分的。海德格尔一针见血地指出,“把‘实体’的存在特征描画出来就是:无所需求。完全不需要其他存在者而存在的东西就在本真的意义上满足了实体观念”。[7]由此看来,“实体”正是万变之中那个不变者,这就已经满足了“本体”的所有特征,如果这不是存在论意义的概念,那还会是什么呢?
人类不遗余力地追寻实体,其初衷是为了给自己确立在世的理由,确立“安身立命之本”。为可变的人生找寻不变的“实体”,通过不变的“实体”筹划可变的人生,这是整个西方传统人学的基本建制和坚硬内核,也是其矢志不渝的信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哲学家们追寻的“实体”是不同的:比如水、火、气、原子等自然实体,灵魂、理念、“我思”、“先验自我”、“绝对自我”、“绝对理念”等理性实体,还有“上帝”“真主”等神性实体,但这些实体所承载的价值是相似的。人类对“实体”“本体”的迷恋并不仅是为获得世界的统一性,更深层次上的意义是要为人类自身寻找“精神之乡”和“立命之本”。它以探求对象之外、之上的超验实体的方式来表达人对生命意义的诉求,为人的生命确立“意义”,为人自身设定“活着”的价值,探求人的存在之根、生命之本,为人类自身构筑理想的“精神家园”,使人能够超越世俗的生存得以“安身立命”,漂浮的心灵得以“安居”。
然而,事与愿违,人类追寻实体的结局使人陷入了“无家可归之境”。我们知道,尽管“实体”一次次地改旗易帜、重装登场,但是,它们的作用机理是相同的:用“一”来遮蔽“多”,以同一性来遮蔽差异性,以虚假的偶像来主宰真实的存在,其结果就是使人陷入“无家可归”之境。这是西方传统人学的最大弊端,这是从古至今的最大迷误,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纠缠不清的一种“幻象”。[8]西方传统人学一直坚守“实体”存在的合理性,却遭遇了不合理性的结局,那就是:人们在找寻“意义”的途中失去“意义”,在营建“精神家园”的途中失去“精神家园”,在确立人的生命意义之根基的同时使人的生命意义在根基处失落。
可见,不管是“实体”,还是“本体”,它们作为终极实在、终极本质、终极真理,始终占据着崇高的位置,支配着人们的全部思想和世俗生活。在“实体”面前,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已经退场,变成了“被赋予思想的石头”。不变的“实体”与可变的“人生”构成了紧张的对立关系。
当然,实体即本体,但实体并非本体论的唯一出场方式。这就是接下来要讨论的“现成本体论”与“生成本体论”的问题。
第三节 现成与生成
纵观哲学史,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本体论传统:一是“现成本体论”(也称“既成本体论”),二是“生成本体论”。相对于“现成本体论”的久远历史,“生成本体论”的出场则要晚得多了。
所谓“现成本体论”,意味着“本体”在万变的情境下具备“我自岿然不动”的品质,具有以不变应万变的本领。“实体本体论”本质上属于现成论性质的本体论。所谓“实体本体论”(Substantive Ontology),是指“我们感官观察的现象并非存在本身,隐藏在它后面作为其基础的那个超感性‘实体’,才是真正的‘存在’,构成了‘存在者’之所以‘存在’的最终根据。‘存在论’的任务就是运用逻辑理性,深入‘事物后面’,进行‘纵向的超越’,去把握超感性的、本真的‘实体’”。[9]一句话,传统人学实体本体论是将现实存在的万物回溯到和还原为一个原始的“始基”和“实体”,在人的生存之外寻求万物的存在根据。
实体本体论的解释原则导致了“人”的遗忘,严重冒犯了“存在”。这种本体论在哲学发展史上将人之为人的根据归结为人之外的“实体”。或者认为人来自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物质是人之存在的根据;或者认为上帝是人之为人的根据,上帝是人之存在的本体论基础;或者认为“至上理性”“绝对精神”统摄人的一切,理性成为人之存在的本体论依据。在实体本体论的视界内,哲学关注的是“什么存在”这样实体性、知识性的问题,而这只是关于“存在者”的问题而非“存在”的问题。
实体本体论传统肇始于古希腊,绵历2000多年而长盛不衰。2000多年来,“实体”一次次改头换面,一路狂飙、高歌猛进,终于在黑格尔体系中得以集大成,也正是在黑格尔那里走上了终结之路。实体本体论的僭越必然导致对实体主义情结的整体性反叛,随着黑格尔的去世,彻底清算黑格尔的哲学遗产成为当时德国哲学界的时髦。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同时标志实体本体论的终结,标志本体论传统的整体断裂,标志西方哲学迎来了重生的曙光。生存论的转向,生成本体论道路的开辟,是19世纪西方哲学史上发生的革命性事件。这一“转向”的实质在于,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废黜“实体”,转而面向人的生存本身来解答“存在之谜”。
所谓“生成本体论”,意味着“本体”不是某种万变不离其宗的不变者,不是虚无缥缈的存在者,而是生成着的、历史性呈现与展开的“存在”本身。马克思、克尔凯郭尔等是生成本体论路向的决定性开辟者。在马克思看来,能够担当本体之重任的不是某种超感性的实体,而是感性实践活动及其历史性展开。在生成本体论的视界中,不是逻辑和知性支配流动的生命,而是流动的感性活动具有无条件的优先性,并且构成逻辑和知性的本体论基础。这种本体论关注的是与人的生存和发展内在相关的“生存性”问题,关注的世界是人生活于其中的世俗世界。哲学只有立足于生活,脚踏坚实的大地,才能获得可靠的根基;只有摆脱抽象和思辨,越过逻辑和知性,回归感性与生活,才能获得“改造世界”的能量。
现成本体论与生成本体论的区别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其一,现成本体论预先拟定一个超验的世界本质,世界的发展就是验证这一设定,完成这一设定,因而具有封闭性;生成本体论则注重世界的自我生成、自我实现,因而具有开放性。其二,现成本体论注重用不变的实体解释可变的生命现象,具有机械性;生成本体论注重“存在者如何存在”,体现为过程性。其三,现成本体论注重在先验世界中追寻抽象不变的“一”,因而具有超验性;生成本体论注重人的感性生存活动的根基地位,因而具有经验性。其四,现成本体论无视现实的人的创造个性和主体性,因而具有不变性;生成本体论则是注重现实的人的差异性和主体性,因而具有可变性。其五,现成本体论把完整的人肢解为支离破碎的人,因而具有非人性;生成本体论把人的社会性和精神性、现实性和理想性、经验性和超验性统一于人的生命活动之中,因而具有属人性。
总而言之,生成本体论的出场是人学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它拯救了实体本体论对人的“存在”的遗忘,宣告了实体本体论追逐的“超验世界”的破产,颠覆了实体本体论“超历史”的本体论诉求,也终结了实体本体论对“理性万能”的迷恋,为哲学通达人的现实世界、观照人的现实生命开辟了道路。
第四节 在者与存在
存在论,即关于“存在”的学问。在哲学史上,巴门尼德第一次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古希腊哲学的主题形态就是存在论。但是,“ontology”这一词的出现则是17世纪的事了,是由德国经院学者郭克兰纽首先命名,并经由沃尔夫加以完善和系统化的。“ontology”这个词的词根是希腊语“on”(拉丁文ens,英文being,德文sein)。根据英语的语法规则,being指的是以个别的方式存在的人和事物,我们一般称之为“存在者”;Being,则解释“存在”,“存在”是一切存在者的总体、总和。“存在”作为最高的总概念,它统帅一切存在者,具有本源性和超验性。也就是说,“存在者”和“存在”本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而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一个重大失误或者说错觉就在于:误将“存在”的问题归结为“存在者”的问题,导致“存在‘存在者’化”,长久以来,这一笼罩在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头上的迷雾始终挥之不去。
“存在论区分”是海德格尔的贡献。“存在”和“存在者”,是理解存在论的重要概念。“在”(sein),也即“存在”,是指存在物的显现、在场,不是指具体的、现场的存在物。“在者”(dasein),也称“存在者”“存在物”,是指已有的存在物,包括一切已经显现出来的现实的存在物和尚未显现的观念中的事物。海德格尔认为,“存在”本身是使“存在者”成为“存在者”的那个东西,是使“在者”成为“在者”的活动过程,是使“在者”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是使在者“在起来”的事实。因此,根据海氏的观点,相对于“存在者”,“存在”在逻辑上具有无条件的先在性,在地位上具有无条件的根基性;一切“在者”首先必须“在”,然后才有可能成为现实的、确定的“存在者”。没有“在”的前提,没有“在”的过程,没有“在起来”的事实,就没有“存在者”。“在”是“在者”的根据和前提,“在者”是“在”的结果和呈现。可见,从逻辑上来说,“在”较之一切“在者”而言,具有优先地位。
鉴于“在”所具有的逻辑先在性,那么,如何通过“在”的事实揭示“在”的意义呢?海氏借助了现象学的方法——“回到事实本身”。然而,“在者”是繁多的,绝大多数的“在者”对自身“在”的生存结构和方式是无所察觉和体会的,因而也就无法揭示自身“在”的意义。唯有“人”这个特殊的“存在物”才可能提出“在”的意义问题,才可能体会和察觉“在”的生存结构与生命历程。海氏将“人”这个独特的“在者”称为“此在”。海氏认为,“此在”与一切“在者”相比,具有两个方面的优先地位:一方面,“此在”优先于其他一切“在者”,只有“此在”能追问自己的“在”,而其他“在者”不能;另一方面,唯有通过“此在”方能领会“在”的意义,不仅领会自身“在”的意义,也能领会其他一切在者“在”的意义,绕开“此在”断不可能。可见,“此在”开启了通往其他一切在者“在”的通道,一切其他“在者”的本体论都要通过“此在本体论”的中介才能得以澄明,世界万物唯有通过“此在”的介入才能得以呈现“在”的生命结构,通过“此在”的澄明才能获得“在”的意义,“此在”之在世成为揭示存在意义的一把钥匙,正是“此在”构成了追问一切存在者存在意义的本体论基础,这就是海氏的“此在本体论”。
根据海德格尔的研究,传统人学在本体论追问的道路上导致“存在‘存在者’化”,而现代哲学在本体论追问的道路上比较注重让“存在者‘在’起来”。传统形而上学,从柏拉图一直贯穿到黑格尔,它们的重大偏失就是没有了解“在者”究竟怎样“在”以前就予以先行断定,以对“在者”的研究代替对“在”本身的研究,没有回答“在者怎样在”的难题。存在物的呈现不是因为“存在者”的眷顾,而在于“存在”本身的光辉;离开了“存在”之光,一切存在物本身都是蔽而不明的。海德格尔的这一看法与马克思有旁通之处,马克思认为现实世界是一个不断展开、不断生成的过程,不存在某种既成不变的本体世界对现实世界的牵引、规定、宰制。同样的道理,人本身也是在自身的感性活动中生成为现实的人并向着理想的人跃迁,并没有一种凌驾于人之上的、万变不离其宗的“实体”来拟定人的生存过程,人的伟大与崇高并不需要人之外的实体来裁定,人的地位与价值也不需要人之外的实体来赋予,人的一切荣耀与光环都应该归功于人自身的存在。
第五节 是与应该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与“应该”不同于伦理学中的“事实”与“规范”问题。在这里,“是”属于存在论的问题,“应该”属于价值论的问题。或者说,存在论回答“是”的难题,价值论回答“应该”的问题。
“是”与“应该”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存在论与价值论的关系问题。从哲学史的变迁来看,“是”最终都指向“应该”,存在论都内含价值论的意蕴。我们大概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缺乏价值维度的存在论是无效的,缺乏存在论根基的价值论也是无效的;或者说,缺乏价值关怀的存在论是不存在的,缺乏存在论支撑的价值关怀也是漂浮的、无根的。
西方传统人学对“人是什么”的存在论问题的回答是错位的,导致了对“如何对待人”的价值论问题的解答也是扭曲的。在实体本体论的视界中,实体即主体,而真正的主体——人则遁入无形,“以人为本”仍然是一个尚未真正开启的意义领域。因为在西方传统人学那里,“实体”的特质与“人”的本性之间发生了颠倒:“实体愈是神圣,人就愈是罪恶;实体愈是独立,人就愈是失去独立;实体愈是自由,人就愈是受到禁锢;实体愈是高尚,人就愈是沦为低俗;实体愈是完善,人就愈是被肢解;实体愈是在场,人就愈是退场;实体愈是万能,人就愈是无能;实体愈是提升为主体,主体就愈是沦落为非人”。[10]总之,只要实体凌驾于人之上,人就无法摆脱实体的宰制。比如,中世纪宗教神学本体论对“人是什么”的回答是:“神是人的最高本质”,人是上帝的作品;因而对“应该如何对待人”的回答就是:灭绝人欲,服从上帝。在上帝主宰人间的条件下,不可能有人的主体性和自由。费尔巴哈和马克思都意识到,不推倒神就不可能恢复人的最高权威,“因为这些神灵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灵同人的自我意识并列”。[11]再比如,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对“人是什么”的回答是:人“属于精神概念本身的一个必然环节”,[12]只不过是精神概念(绝对理性)自我运动、自我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节点;因而对“应该如何对待人”的回答就是:服从绝对理性是人的天命。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没有给人的独立性和自由留下充足的空间。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批判道:“在德国,对真正的人道主义来说,没有比唯灵论即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它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并且同福音传播者一道教诲说:‘精神创造众生,肉体则软弱无能。’显而易见,这种超脱肉体的精神只是在自己的想象中才具有精神力量。”[13]总之,人本向度的遮蔽与实体的僭越是西方传统人学的一体两面。
与实体本体论不同,生成本体论的最大贡献不在于拯救了本体论的未来发展,而在于开启了人本价值的新视野。马克思人学本体论对“人是什么”的回答是:感性活动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非常深刻的基础,也是人成为人非常深刻的基础,我将其称为感性生活本体论。[14]感性生活本体论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价值空间。在这个价值空间里,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必须通过人的感性活动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乃至整个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必须通过人的感性活动,在“政治解放”的基础上追求“人类解放”,在“解释世界”的基础上力求“改造世界”,在“反思现实”的基础上力求“超越现实”,才有可能成为现实。感性生活本体论说明,人的伟大与崇高只能归功于人自身,人的世界只能“以人为本”。感性生活本体论还说明,社会生活理应以人为本,而不是以任何别的先验实体为本。总之,感性生活本体论不可能是与人无涉的和价值中立的,而是注定包含人本价值的意蕴。
感性生活本体论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所建立的各式各样的“实体形而上学”,将人的世界还给人自己,将人类社会归属于人自己。社会历史不是超验“实体”的杰作,而是人自己的作品,是人的感性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展开。人类历史绝不能还原为某种抽象的实体,既不能像自然主义哲学家那样还原为抽象的“自然物质实体”,也不能像理性主义哲学家那样还原为抽象的“精神实体”,更不能像神学家那样还原为抽象的“神性实体”,而只能还原为人的感性生活本身。因此,任何反人本化的价值取向(比如物本、神本、君本、钱本等)都是一种本末倒置、舍本求末的表现,只有“以人为本”才是人类社会的现实选择。
(本章内容原载于《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注释
[1]本书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存在论”和“本体论”这一概念。
[2]〔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12,第137页。
[3]钱学森:《要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人民日报》1990年8月14日。
[4]〔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第172页。
[5]〔荷兰〕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3,第3页。
[6]〔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64页。
[7]〔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第108页。
[8]〔德〕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第516页。
[9]贺来:《马克思哲学与“存在论”范式的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10]陈曙光:《存在论传统的断裂与重建——马克思人学革命研究(下)》,《探索》2014年第4期。
[11]马克思:《博士论文》,人民出版社,1973,第3页。
[12]〔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9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第7页。
[14]详见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