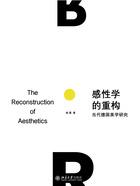
第三节
假象与真实
在这个以“显现”为核心构建起来的理论大厦之上,就可以开始对各种复杂的审美现象做出解释,也可以对各种潜在的挑战做出回应。
其中一个对显现构成挑战的就是审美现象中频频发生作用的“假象”。假象,泽尔把它界定为“在感性上具有事实性之外的当下性的事物”[60]。假象在审美遭遇中频频出现,比如自然界的海市蜃楼、艺术中的灯光装置作品。审美假象与日常假象的不同在于,日常假象具有实践上的妨碍性和认识上的欺骗性,它是有待纠正的,不然就有负面后果;审美假象不同,它不因为揭穿而消失,它受到欢迎,积极参与显象间的游戏,成全一个得到强化的当下。假象是审美中的一个特例,但也是审美活动之为显现事件的经典证据。因为,在对假象的欣赏中,审美的那种“本体论漠然”[61]达到极致。它凸显了审美并不关心对象的存在,只关心实际显现。所以,泽尔有个说法:“假象是真实的。”[62]作为一个事物,它是假象;作为一个因素参与显现事件,它是真实的。正因为审美关注的是一个时空当下的活动本身,而不是对象的事实性存在,假象在审美中获得了积极意义,是对显现的成全。
跟假象相似又不同的是“想象”,它也同样是对当下的拓展。假象虽然不符合事实,却具有当下在场的特点,而想象中的事物却并不在场。审美想象跟普通想象有所不同,它具有所有审美意识共同的一个模式:审美想象是在当下进行的想象,并且也是对一个当下的想象;它是显现中的想象,也是对一个显现事件的想象。艺术中主要运用了审美想象。艺术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似乎依赖的是一个跟当下事实完全不同的另外事物的想象性呈现,但泽尔强调,即便如此,这种呈现,首先也是通过文本自身的呈现而呈现的。
这里就涉及艺术作品的媒介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传统认为音乐的媒介是声响,绘画的媒介是颜料,文学的媒介是文字,等等。泽尔看法不同,从显现美学的视野出发,他认为艺术的真正媒介既不在材料,也不在材料的运用,而在于材料所构成的“显象间布局”[63],其实也就是“显现”,艺术的媒介是显现。因此,任何艺术,它的首要特征是表现,更确切地说,是通过自我表现,让某物得以表现。艺术作品的重点本来就不在于物理事实,而在于它所具有的双重表现力。从这一点出发,泽尔提出了“象征”与“表征”[64]之间的差异,艺术作品不仅仅是象征符号,它自身也是它所指涉的事物的一个“范例”。因此,泽尔提出了一个非常犀利的观点:不是具象艺术,反而是非具象艺术揭示了艺术(图像)的本质。[65]因为,在抽象艺术身上,我们更明显地看到了艺术作品自我显现的特征,而不是传统欣赏习惯中对再现他物的依赖。与此相关,泽尔使用了“不透明”[66]这个概念。艺术作品的特征在于它的不透明性,如果你要从中看到某物,你首先得看到作品本身的呈现。一个事物的表达活动越不透明,就越有审美性和艺术性;越透明,就越失去审美性。前者是阅读文学作品的情形,后者是阅读洗衣机说明书的情形。
从这样一个显现美学的基本艺术观出发,泽尔就进入了对一个最大挑战的反击中。这个挑战来自阿瑟·丹托和他所依据的杜尚为代表的当代先锋艺术。看上去,20世纪的艺术似乎已经“把感性的罪过从艺术理论的神庙中驱除”[67]。现代艺术似乎毫不留情地远离了感性,也就是说,远离了审美。在丹托看来,和其他日用品在外观上无异的现成品能够进入艺术,这证明现代艺术已经与审美(感性)脱钩了,如今,决定一个东西是艺术的关键,不是看得见的东西,而是某种不可见之物,即艺术家与观众的观念,艺术界的授权。[68]泽尔对此的回应是,首先,事物的感性外观从来就不是审美的核心,审美的核心是当下的显现,不仅两个看上去无异的事物并不具有同样的(可被现代艺术否定的)审美属性,哪怕同一个事物,在不同的情境中,也具有不同的(纯粹的、气氛式的、艺术的)审美属性。既然审美的核心不在对象,而在显现,那么,不管你拿什么对象来充当艺术作品,也不妨碍它显现。其次,杜尚的现成品也并没有脱离显现,反而成全了显现,因为它自身虽然是现成品,但是在欣赏中并不是作为现成品而被直观的,它依赖一种当下发生的冲突,在期待与落空之间的落差,以及造成的独一无二性。对传统显现的期待落空,恰好成全了一种更为强烈的显现。杜尚的作品,要实现对传统艺术观念的嘲讽,它也依然遵循其他艺术作品所遵循的双重表现力,即通过自我表现,让某物得以表现,它的物理事实可以被一模一样的另一个现成品替代,但它所展示的那样一种事态,却是普通事物所不具有的。杂货店的雪铲或小便池无法实现嘲讽。因此,现成品的表演也依然是一种当下的显现。
比现成品更为极端的例子,是那些根本不可见的艺术,比如德·玛利亚(Walter De Maria)在1977年为第六届卡塞尔档案展创作的《垂直的大地公里》(Der Vertikale Erdkilometer):一根长达千米的空心管插入大地深处,表面只看到一块简单的黄铜盖子。这个作品似乎不再感性可感。但是,泽尔说,正是因为可见与不可见的冲突,在面对这个作品时,它所唤起的人们对空间的当下意识比耸立的雕塑还多。在书中,泽尔还对来自文学的潜在挑战做出了应对,他指出:文学这样一种在感性上无法直接可感的艺术形态同样具有显现特征,因为,只要是文学,它就有不透明性,就通过自身的音调、节奏、韵律及其布局的呈现来呈现他物。
除了分析这些典型的艺术、审美现象背后共有的显现特征,泽尔还对一些典型个案进行了显现美学的演绎。他讨论了“杂音”作为一种审美显现的临界状况所揭示出的“无事件的事态”[69]的审美可能性,以及艺术杂音中“被赋形的无形性”[70]特征。他集中讨论了“图像”问题,援引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的“密度”理论分析了图像与普通符号之间的根本差异,强调图像的基本特征是通过自我指涉来指涉他物,从而表现优于再现。图像既是在世界之中的一个事实,又是关于世界的一个表达。这是一种“在某物中看某物”[71]的能力。这是柏拉图走出洞穴又重回洞穴所见到的投影这一理想认知过程在审美实践中的一个暂时实现。因此,图像(艺术)观照带给世界的不是更多虚幻,而是更多真相。[72]
在本书最后,泽尔还用显现美学对“暴力”艺术做出了分析,值得一提的是,他认为艺术的暴力不在于再现暴力的内容,而在于艺术本身形式上的暴力,对暴力的暴力性[73]的揭示。从广义上来说,艺术本身就是对人的规定性的打破,这已经是一种艺术暴力。因此,艺术暴力的实现,有时候甚至要靠更少的暴力内容来实现,因为老调重弹的暴力叙事本身已经失去力量。
对杂音、暴力、电影乃至体育的研究,彰显了显现美学的解释力及其开放性。
泽尔这本《显现美学》页数不多,但内容层次相当丰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高度“密集”型的。作为一本理论著作,它做到了相当透明,能让人清晰、精确地进入问题深处,谨慎地辨别同异,获得超出成见的洞见。沿着他所构建的一条条通道,沉得住气的读者经常会在尽头处看到喜人的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