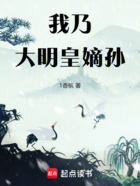
第104章 嫡长承统,国本永固
朱标更是不顾龙颜大怒,当众严词驳斥:“庶母并无子嗣,太子岂能僭越礼法,行此大礼?”结果,朱元璋盛怒之下,竟持剑追砍朱标,幸得马皇后及时以画像阻拦,才避免了一场悲剧。
此刻,帝王眼中那森然的寒意,与当年竟如此相似,仿佛时光倒流,一切都未曾改变。
“父皇既然对雄英心存疑虑,为何不亲自考校一番?”朱标突然抬头,眼中闪过一丝决绝之色,犹如破釜沉舟般坚定,“若他果真不堪大任,儿臣愿辞去东宫之位,以谢天下!”
朱元璋听到这话,顿时怔住了。
他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到几年前批阅的邸报上,那时朱雄英在春和宫教导幼弟,面对侍读学士的提问,竟以“百姓无粟米充饥,何谈忠君”的精妙问答,令侍读学士惊叹不已,直呼“此子胸襟,远超同龄”。
然而,帝王之心深似海,他下意识地抚摸着腰间玉带,那是马皇后临终前亲手为他缝制的,承载着无尽的回忆与深情。他长叹一声,语气中满是无奈与沧桑:“当年你母亲也是这般苦劝于我,可结果又如何呢?唉!”
两人在殿内静默了半个多时辰。
朱元璋猛然转身,龙涎香混合着空气中淡淡的血腥气扑面而来,他冷冷地说道:“明日让钦天监择选吉日,为英儿举行嫡孙册封礼。但你要牢牢记住,这大明江山,姓朱,不姓仁!”
殿外,风雪骤然加剧,狂风呼啸,雪花纷飞。毛骧望着武英殿内那明灭不定的烛火,心中感慨万千,不由自主地想起二十年前那个跪在雪地中的少年。
那时的太子殿下,风华正茂,心怀天下,又何曾想过,有朝一日,会为了巩固储位,将年仅十五岁的朱雄英无情地推上这风口浪尖?
他忽然又想起宫廷内一则绝密密报,那是刘伯温临终前留下的谶语:“文忠(朱标)之死,不在流年,而在骨肉相残。”
寒风如刀,卷起满地的奏折,朱元璋最后的那声叹息,终究还是湮没在了这纷飞的雪片之中,无声无息,却又仿佛预示着一场无法避免的风暴即将来临。
这一夜,大明皇帝朱元璋独自在殿内待到破晓,最后深深叹了一口长气,又仿佛下了某种决定,毅然决然看着春和殿的方向。
洪武二十三年四月初一,奉天殿玉阶映着晨曦,朱元璋高坐龙椅,目光扫过殿下黑压压的文武百官。
殿角蟠龙香炉青烟袅袅,将“皇明祖训“四个鎏金大字映得灼灼生辉。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司礼监使司尖细的嗓音穿透晨雾。
“朕以眇躬,膺受天命,肇基江左,廓清华夏,践祚以来,兢兢业业,唯愿大明昌盛,百姓安乐。
今皇太子朱标嫡长子朱雄英,日表英奇,天资粹美,恪守孝道,勤勉向学,深肖朕躬,允协天心。
祖训有云:“皇太子嫡长子为皇太孙,次嫡子并庶子年十岁皆封郡王“。今册立朱雄英为皇太孙,正位东宫,以重万年之统,以系四海之心。自即日起,当竭尽心力,悉心辅佐皇太孙成长,如事朕躬。
待及年岁,佐其父皇太子朱标,共担大明重任,为我大明开万世太平。
钦此。
洪武二十三年四月初一”。
待宣读完毕,朱元璋站起身威严的脸庞浮现在众位朝臣面前。
龙口轻启。
“另一份诏书也宣了,朕希望尔等尽心尽力辅佐太子和皇太孙!”
有些精明的人已经猜了出来,辅佐二字已够。
司礼监使司一顿,朝堂众位大臣抬起头,接下来就要看哪些是朱元璋钦点的朱雄英的辅佐之人了,这才是重头戏,一步登天?从龙之臣!
司礼监使司抬头看了一眼殿内朗声道。
“皇太孙乃国本之重,教育尤关根本。
特命:
蓝玉为太子太傅,掌训导之责,教以兵略,俾知金戈铁马之业;
徐达为太子太师,授以帝王之道,导以仁德治世之理,示以金石之坚;
宋讷为太子少师,专司经史典籍,启以圣贤之学,树以文治之基;
宋濂为太子少傅,授以诗书礼乐,正以文辞雅韵,成以德行风范。
师保之责,重于山岳。尔等须恪守师道,尽心辅弼,若有懈怠失职,朕必严惩不贷!
钦此”。
众位大臣抬起头,蓝玉,徐达,担此任都在合理之中,但宋讷为太子少师确实出人意料。
宋讷出身官宦世家,一直到洪武十六年才人国子监祭酒,宋讷以“学以致用”为教育理念,严立学规,推行积分制与坐堂考勤,整顿国子监学风。
洪武十八年科举中,四百七十余名进士中太学生占三分之二,朱元璋赞其“训迪有功”。
六名金甲武士抬着雕龙漆盒鱼贯而入,朱元璋亲手解开赤金蟠龙纹锦袱,露出玉圭、册宝与金册。
朱雄英身着衮冕,旒冕冠垂下玄色丝绦,腰间蹀躞带悬挂着马皇后临终前缝制的羊脂玉珏。
他按着《皇明祖训》礼制,先三跪九叩谢恩,再捧起刻有“雄英遵祖训“的玉圭,声音清亮如钟:“孙儿谨遵祖训,以法礼治天下,不负皇祖父托付!“
殿内响起零星私语。
礼部尚书李原名捻着胡须暗自点头——这个少年虽生于深宫,却深谙“嫡长为尊“的祖制精髓。
朱元璋突然抬手止住群臣山呼:“且慢!”
他命人抬过一卷黄帛,展开宣读:“着令工部于钟山之阳筑'太孙殿',遣礼部考订皇太孙祀典,命翰林院纂修《太孙实录》!”
殿内霎时寂静,所有人都听懂了这“另立宗庙“的深意——朱雄英的地位已超越普通储君。
朱雄英心里暗暗叹了一声,皇祖父和父亲为我做了太多了,责任重大。
朱雄英拜谒太庙后,礼部制定明日各亲王与皇太孙相见仪制,规定亲王需向朱雄英行四拜礼,体现其尊贵地位。
暮色中的紫禁城笼罩在暮霭中。
朱雄英站在奉天殿屋檐下,看着六部官员鱼贯而出。
他摸着腰间新佩的“山河同寿“玉佩,想起前些日子与蒋瓛的对话——这个被父王戏称为“狐狸”的男人,此刻正带着二十七名番薯种植使臣,悄然潜入山东驿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