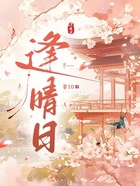
第22章 稚子兵刃
于这千钧一发生死之际断臂,似非明智之举,但凌轲无比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他在做一件唯他可做之事。
或许是因为那八字示警之故,凌轲在反复思量之下,内心深处已存了一丝预感。
得益于那一丝预感,他才能从今日这突如其来的惊乱变故中保有一份冷静,透过这层层表象看到仙台宫之祸背后真正的根由——
太子突然背负上了以巫术谋害君父的嫌疑,这固然触碰到了天子的禁忌逆鳞,可十数年的父慈子孝,陛下无论如何也不该不给太子任何申辩的机会,竟直接下令让手段残暴的绣衣卫首领祝执前去问罪太子。
天子的怒气来得太过汹涌,也太过决绝。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此事不过是一粒火种,只是火种飞落之处早已铺满了火油。
这火油是陛下心中压抑掩藏了许久的不安,而这诸多不安正该与他这个太子舅父有关。
根由在他。
那灭门之祸的屠刀原是为他而来,太子突然卷入刀下不过是一场意外……是有心者察觉到了那把屠刀已经举起,遂趁机将太子一并推向了刀锋之下!
凌轲自然知道他杀去仙台宫,逼至宫门前,如此举动,无论如何已再不可能为君王所容。然而属于他的死局本就已经布下,便也不存在自绝生路,一切倒因为果的顾忌挣扎都没有丝毫意义。
这是人心造就的死局,唯有借人心裂痕才有希望替思变破开一丝生机。
哪怕自此后,陛下与思变之间注定隔阂乃至陌路,但只要能在今夜换来一寸缓冲喘息之地,思变就至少还有活的希望,能活,就能有机会去查明真相。
凌轲的下属惊慌失措地为他包扎断臂之处,凌轲面色青白,用仅剩的一只手紧紧捂住简单包扎的伤口,鲜血源源不断地从指缝间涌出。
他手中仿佛紧攥着一根长长的弓弦,那弓弦绷紧到了极致,将他的手心割得鲜血淋漓。
弦的另一端遥遥握于帝王手中,而弦身之上,附着着无数人的生死性命。
——该动兵一搏吗?
纵然已将虎符归还,但凭借凌轲在军中威望,纵无兵符在手,他也未必不能强行调动城外三中之一的兵力,这足够挑起一场浩大而持久,一旦开启便会有各方人心介入、不能轻易停下的厮杀。
可他在与谁厮杀?——那余下三中之二,亦是跟随他出生入死的将士。
供他厮杀的战场又在何处?——脚下这片土地之上,是他用十数年的拼杀与无数将士白骨,才得以勉强铺出的太平初象。
这场厮杀之后的胜者是谁?——不会是他,甚至也不会是君王,更不会是无辜百姓,只会是隔岸观火的始作俑者而已。
准确判断一场战争的代价胜负走向是他唯一擅长的事。
而这些都绝非凌轲想要见到的结果。
人人都有自己的坚守,他原本就是个不知变通的匹夫而已。
他断的不仅是一臂,他私闯至此,罪名已定,他在告诉君王,他可死,他愿死,他凌轲宁可自断而亡亦不为祸国之剑。
只求君王见他此心,不要殃及更多无辜之人。
凌轲紧紧攥着那根无形之弦,眼中含着泪,看向那巍峨的宫门,等待着弦的那一端传来回音。
天下真正大统尚不足百年,六国史书与诸子百家著作曾被焚烧一空,大乾虽建,但刘家江山可以依循的先例实在太少,有关大国社稷之经验也还未来得及累积——
足下踩着这样一片前所未有的开阔土地,昔日的仁帝也好,凌轲也罢,他们都自认走在一条全新的道路上,他们志同道合,彼此欣赏,意气风发而又对大乾的江山版图充满了野心规划,于是他们几乎是理所应当地认为自己没有任何道理会步前人后尘,他们理应开启新天地,什么君臣离心鸟尽弓藏疑心生暗鬼?皆不过无能者所书昨日迂腐狭隘之旧诗篇。
然而此时,凛风呼啸而来,还是翻到了这诅咒般的一页。
或许这才是真正的巫咒。
若无可挽回,那便尽量削弱这代价吧。
相识多年,纵然不知何时竟已不再相知,但臣与君之间,理应还保有这一丝“共识”与“默契”存在。
然而这份被凌轲笃信着的“共识”与“默契”却未曾有机会被验证。
仁帝在昏厥之前,听到的最后一道急报,是长平侯抗旨杀去了仙台宫救下了太子,正在向正宫门杀来的消息。
仁帝几乎是双目赤红地看向了手边压着的一封密奏,那是长平侯通敌匈奴的罪证,早在两月前便秘密递到了他的手中,他隐而未发,甚至仍有一丝犹疑不定……他并不欲让太子牵涉其中,故才令太子去往仙台宫祈福。
可谁知他的太子借祈福之名行诅咒之举,他的皇后反了,凌轲果然也反了!
仁帝胸口气血翻涌,脑中最后一丝理智也荡然无存:“拟朕口谕,今夜胆敢犯近宫门者……不惜代价,格杀勿论!”
于是当凌轲断臂的消息传至未央宫正殿时,回应那传话禁军的便是这一道格杀勿论的御旨。
郎中令薛泱纵有百般不忍,却也不敢不遵,长安内外局面瞬息万变,说不定已有消息被送到了城外军营中,没人能担得起这代价。
而在薛泱下令动手之前,后方负伤的绣衣卫首领祝执已策马追至此处,他见得宫门前对峙的情形,怒然质问:“大胆薛泱,待犯禁者视而不见,莫非逆贼同党?!”
薛泱色变之际,祝执所领禁军已举刀杀上前去,而祝执在马背之上挽起了手中长弓,箭矢刺向凌轲所在。
凌轲凭一臂尚可挥刀挡落这支箭矢,然而更多的箭矢很快逼至。
满身是血的少年向他扑来,将他护在身下。
但如此局面之下,已是谁也无法去护住谁了。
刘固浑身扎满了箭矢,凌轲身上也很快遍布血洞。
椒房殿中,凌皇后立于高阁之上,一名武婢单膝跪在她身侧,送来了宫门外的消息。
凌皇后闭了闭眼睛,眼底却无悔也无泪。
走到这一步,不是她的错,不是思变的错,更不是她阿弟的错,既然无错,为何要悔?而既已在这绝境中拼尽全力无愧于心,便也无需有泪。
“既荷——”
“婢子在!”
“带虞儿和从南一起离开,去寻思退,告诉他,让他听话,一切到此为止,退得越远越好。”
武婢既荷闻言抬起头:“小君,那您……”
既荷话未说完,惊惧地伸出手去,却只来得及抓到那华袍一角。
正月春夜中,凌皇后自高阁上空一跃而下。
风雪过耳,死亡来临前的一瞬,她脑海中快速闪过了这一生的经历,最终定格在了幼时和阿弟一起放羊时,在草地上赤足奔跑的画面。
一日放羊时,听到了马蹄声,她拉着阿弟躲在大树后,看到一队人马疾奔而过。
那队人马装束并不威风,乍一看不过是这乱世之中并不起眼的一支乱军草寇,他们的刀剑有些破旧,只旗帜上绣着一个还算醒目的字,她那时不识字,直到很多年后,她才知那原来是个“刘”字。
从此后,她和阿弟便和这个姓氏纠缠相连,至死方休。
远归的马蹄似从凌皇后的旧梦中奔出,马背上载着的是她并不听话的小儿子。
正旦前夕,刘岐奉母亲之命,去往长安两百里外为父皇寻访一位仙医。
刘岐不是很想去,他才回来没几日,且他昨日还和母后说过他心间疑虑,母后不给他开口的机会,含笑对他说,向他父皇尽孝才是正理。
刘岐想了想,似乎也对,父皇是这天下之主,只要能让父皇欢喜安心,想必没有什么劫难是破除不了的吧?
况且,当真会有什么劫难凭空发生吗?
他离京前两日去见父皇,父皇还拿了把桃木剑丢给他,说要试试他的剑法可有长进,他志得意满,父皇累得气喘吁吁,就坐在殿门前的石阶上,说只怕再有两年,便要输给他这顽劣小儿了。
他来不及得意,父皇转而要考问他的经史,他心里发虚,去向走来的兄长求救。
父皇那天分明还笑得很开心。
可此时……
提早归京的刘岐一路策马冲到宫门前,看到的是舅父和兄长残破的尸体。
他身侧随行的四人是御前禁军,持天子令节,故而一路无人敢拦。
与此同时,一名禁军由宫内而出,带来了凌皇后伏诛的消息。
伏诛,伏诛?
刘岐瞬息间已分不清虚实,也听不到任何声音了,他只看到祝执手里提着剑,去拨弄舅父破碎的尸身——
于是他拔剑冲上前去。
然而须臾间,不知何处飞来一支短箭,倏然钉入了他的左腿中,阻止了他的脚步。
刘岐猛然一跪,仍要再起身,而祝执已冷笑着示意手下之人向他的方向开了弓。
“大胆!”
随着一声怒斥,墨色的披风挥开,一道威严的身影挡在了刘岐身前。
祝执微眯双眼,看向那丝毫不知避嫌,竟赶来了此处的鲁侯冯奚。
老人声音有力:“且不说稚子初归,不明事态!其乃陛下之子,如何处置唯有陛下可以决断,胆敢僭越者,皆当以谋害皇子之罪论处!”
鲁侯蹲身下去,紧紧抱住了那个满脸恨意泪水的孩子。
作为马背上打天下的开国功臣,鲁侯纵已上了年纪,却也足以将一个受了腿伤的孩子牢牢箍在怀里。
刘岐不知道自己被鲁侯这样禁锢了多久,他在这赤红的雪地里悲吼着,挣扎着,如同置身炼狱。
不知过了多久,无数脚步匆匆掠过,直到一人停在刘岐面前,慢慢蹲身下来。
被血染红的雪地中,一只锦盒静静躺着,里面盛放着的几粒褐色药丸散落开来。
那是刘岐为他的父皇求来的“仙药”,那名“仙医”年迈,行动迟缓,刘岐为了快些回京,让人在后方护送医者,自己昼夜不停率先赶回。
此刻,那药丸被来人一粒粒捡回到了锦盒之中,递向刘岐。
刘岐循着那只递还锦盒的手,看向眼前这位蓄着短须,面孔严正,看起来永远不近人情的严相国。
对方赠予了他一句话。
“此乃稚子兵刃,六皇子当善用。”
稚子即便有再多的怨恨,也注定杀不出这铜墙铁壁禁军重围。
稚子应当握紧稚子该握的“兵刃”,用这“兵刃”为自己争来活着长大的资格,乃至更多其它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