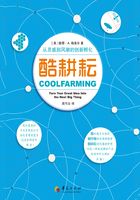
二、群体创造力——酷耕耘的动力
志愿者们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最好的翻译工作,他们不在乎花费自己多长时间……这是一种激情,一种做职业枪手也得不到的激情。
——摘自TED媒体执行制片人琼·科恩的《志愿者的翻译质量》[1]
没什么比全身心投入的群体更有创意的了。尽管一些聪明且勇于奉献的个体提出了许多开创性的新想法,但是如果他们没有特定的群体支持的话,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发明者个体在自己的作坊里独自摆弄,或者甚至在一个大公司的科学实验室里面做研究,都是无法成功的。只有群体的集体努力才能使一个个伟大的想法成为现实。目前,在互联网经济环境下,有许多案例可证明这一事实,比如我们上面看到的万维网和开源软件Linux的建立和发展。一些商业公司,如宝洁、乐高和谷歌,也正是在遵循这一原则的基础上蓬勃发展的。
这些创新团队成员长时间努力工作,取得了惊人的成果——他们这么做的唯一动机是热爱这个新的创意,他们感觉自己是这个团队——一个可能会改变世界的团队的一分子。他们最初的想法不是为了获取经济收益,而是挑战或解决一个难题,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而宝洁、乐高、谷歌等商业公司,也令人信服地证明,在一定的时候,他们的创新也会获得巨大的回报。
创新团队成员不仅具有创造性,更重要的是他们具有群体创新意识。“群体创造力”表示一种积极的行为,这种行为来自于集体意识,并能最终产生优异成果。在生物学中,群这个词用来描述朝着同一方向行进的一群动物的行为。蜂群充分体现了这个概念:没有指挥中心,蜜蜂自组织筑巢,饲养和培育它们后代成长,采集食物,甚至决定谁成为它们的下一个王后。人类一起向同一个创新目标奋进,会产生非常有趣而令人兴奋的潮流。人们蜂拥组群,所释放出的创造力,强于任何只是为满足需求而进行的组织创新。
随着在线交流方式的广泛应用,人类群体创新的能力成倍增长,可快速形成跨国界、跨地域、跨组织边界的创新群体并协作完成创新任务。在大大小小的公司中,一些富有创造力的个体聚集在一起,共同探索感兴趣的创意,不管这些创意是否与公司收入直接或间接相关。这些新群体的核心就是协同创新网络,或称为COINs。
以协同创新网络为基础的群体创新模型基于三个原则。这三个原则是运用群体创造力的一个逻辑推论。
(1)给出力量获得动力。这是最为重要的原则。让每个人都参与协同创新网络,无论他们参与到哪个层次,让他们都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他们具有新的想法,提出了解决方案,以及做出了宝贵的贡献,这将使所有成员都具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意识。这也意味着,在任何时候协同创新网络成员都可自由离开,其他团队成员也不会阻止。
(2)依靠内在动力。这一原则可释放群体创造力,它与赋予群体力量紧密相连,不仅让群体自组织,还提供一个培育土壤让创意开花。这尤其意味着,至少在最初阶段,协同创新网络成员不该因自己是群体的一部分而获取报酬。好的点子可以创造潮流,创意和知识应该在团体或网络中自由分享。如果团队接受这个新创意,则新的协同创新网络就开始成长,这个创意就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团队建设者尽力支持群体发挥潜在创新力,让群体创新产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依靠群体创造新东西。这个初始团队组合不应采取经济激励措施,稍后阶段可能会有经济激励,但至少在开始时,它们只会分散协同创新网络成员对目标的注意力。
(3)发现酷的潮流,寻找很酷的人。优秀的酷耕耘者同时也是很棒的酷狩猎者——想想风险投资人。最好的酷耕耘者都知道,任何伟大的想法都需要一个伟大的团队来实现它,这样的团队也正是风险投资人所需要的。在网络搜寻或寻找下一个很酷的事情时,酷耕耘者寻找的关键就是那些融入网络的领导者,他们不是把自己当作网络明星,而只是作为群成员。然后,酷耕耘者会吸收这些领导者加入自己的事业。
群体创造力的这三项原则在“酷耕耘”中紧密相关,其目标是让具有内在动机的关心事业高于自我的人尽早参与进来。理想的情况是,这些人在他们的团队中倍受尊重,而且甘愿扮演“旗手”或“灯塔”的角色。然后,这些人再吸引其他人加入进来。仅仅作为一个专家或是名人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有高度的“集体智慧”,这一点会在第8章中详述。
现在,我们需要了解“群体创造力”与“群体智慧”之间的区别。这两个词语经常会被混淆。特别是,我们需要将“智慧”和“创造力”这两个词区分开来。
智慧,指的是我们能够理解和应对复杂情形,意识到事情发生的价值,并从不同选项中找到最佳解决方案。计算机科学家埃里克·伯纳博最早提出了“群体智慧”概念,其灵感来自群居的昆虫1。特别是,伯纳博发现了蚂蚁们的智慧——它们通过铺设信息素来共同探索一条通向食物源的最短路径。
创造力则是不同的东西。它意味着建立一些全新的东西,采取看似与要解决的问题域不相关的概念来构建独创方案。这是一种独立的思考,跳出了“条条框框”,用自己的判断来看待问题,而不受常见和流行意见的限制。一些社会性昆虫,如蜜蜂,作为大团队中的创造者,是群体创造力的优秀榜样。蜂群显示了群体创造力的重要模式,共同创造新的蜂房,选择它们的新女王,并寻找最好的食物源。
人类擅长协同创造全新的事物。事实上,人类历史上取得的所有进步似乎都源于群体创造力。用艾萨克·牛顿自己的话来说,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提出了开创性的万有引力,是基于前人的发现,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老阿基米德。任何有独特创意的人都是这样,莱昂纳多·达·芬奇的见解基于希腊和罗马的艺术家、哲学家和数学家的思想;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在发明灯泡和留声机时利用了很多发明家的成果,包括爱德华-莱昂·斯科特·德马丁维尔。事实上,人类越多地建立网络和交流,就越富有创造性。
演化生物学家贾德·戴蒙在他的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2中的论述令人信服:地中海地区之所以成为延续1万多年的文明的历史温床,是因为它交汇了亚洲、非洲北部和欧洲人的不同文化。正是大量人类文化的混合和交融才使它成为最具创新性的区域。来自中国丝绸之路的旅行者、从廷巴克图来的商人,以及来自挪威的北欧海盗船,都聚集在地中海盆地,他们交流知识,相互学习。然而,在被欧亚盆地切断的其他地区,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北美和南美,以及澳大利亚,创新步伐明显放缓,看来创新速度与相互间交流的人口规模成正比。虽然非洲南部的撒哈拉能够独立地发现铁的用途,但在美洲或澳洲的更小群体的人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事实上,在与澳大利亚相邻的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人口更少,到20世纪,那里的部落仍然生活在石器时代。
简而言之:人们越是以网络和群体形式聚集在一起,就会越有创造力。这个事实不仅适用于人类,也同样适用于类人猿。
虽然“创造力”这个词是对人类而言的,但它有时也被用来描绘类人猿。例如,研究人员观察发现,当黑猩猩伸手通过瓦墙孔取食白蚁(食品),若瓦墙孔过于狭窄,黑猩猩的手无法通过时,它会用棍棒捅取白蚁。研究人员进一步观察发现,小群体里的黑猩猩如果有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同伴,那么,它们也会变得富于创意。有些黑猩猩群体不会使用工具,但也有一些群体会经常使用工具获取食物。年轻的黑猩猩还会向它们的长辈学习交换技巧。所以,黑猩猩也有群体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