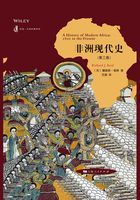
政权、冲突与贸易(1):湖泊地区
英文版原书页码:57
非洲五大湖地区——特别是环绕坦噶尼喀湖、维多利亚湖、爱德华湖和阿尔伯特湖的北部湖泊地带——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成熟的文明发祥地。布干达、班约罗、托罗、安科拉、卢旺达以及布隆迪王国都在19世纪之前就有了文明发端,并且具有某些相似的基本特征。它们是充沛雨水和肥沃土壤的产物,促成了一种较为密集较为稳定的人口状态,超过了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通常情况。它们在政治文化方面也很相似,包括都拥有强大且中央集权的王权,这也具有重要的象征性和仪式性。这一湖泊地区的国王们常常通过王权任命的地方首领来实施统治,但如同王室的谱系一样,首领的世系也开始出现。常常依据功绩来任命这些官员,忠诚无疑会得到回报。而且,王权的一个关键特征就是它通常缺少一个明确的继承人——王室的男性亲属常常会被监禁或被杀,这就意味着继任常常会演变成一场暴力事件。女性在东非一般比在南部或西部地区享有更高的经济和文化地位。这一地区的大多数王国,统治家族都声称自己是移民群体的后代,但准确性不尽相同。在15世纪到17世纪之间来到该地的尼罗河游牧者移民,的确繁衍了一些统治家族,或者是作出了贡献。也有一些则声称自己具有神的地位。围绕着这些特权地位发展出了复杂的上层口述传统,支撑着统治阶级和世系的分化脉络。特权本身以详尽的纳税体制和朝贡体系来维持。移居的游牧族群将这类体系带到了卢旺达和布隆迪,他们在那里被称为图西人,在安科拉则被称为喜马人(Hima)。在这些社会中,他们是农业生产者的雇主,农业生产者则是讲班图语的农民——卢旺达和布隆迪的胡图人,以及安科拉的伊鲁人。[20]事实上,这些群体之间已经有了许多农业和经济上的互动,但在很多方面,畜牧则被认为是统治上层的事情,与较高的地位联系在一起,游牧族群也就成为高级的社会阶层。只是到了20世纪早期,这类社会经济身份才固化为不同的“部族”。
北方湖泊区域的主要王国是布干达和班约罗,这两个国家长久以来密切联系,既有暴力冲突也有友好来往。班约罗由15世纪以来的基塔拉(Kitara)国发展而来,一直是该地区的主导力量,直到17世纪至18世纪,它的土地才渐渐被咄咄逼人的扩张中的布干达王国所掠夺。布干达有着湿润而肥沃的土地,因此拥有密集且相对较多的人口。这样一个成熟而具有竞争力的社会,它的最上层是一个基本上为世俗的国王,或称“卡巴卡”(Kabaka),他在这个国家里掌握任命主要首领的权力。布干达的主要特征就是高度重商的对外政策,寻求控制本地区的经济资源,由一种先进的军事文化来驱动。战争是获得商业、经济和领土支配权的政治手段。到19世纪开始时,布干达支配着维多利亚湖北部和西部地区,处于一种强有力的地位来应对这一时代的挑战,[21]我们下文将看到。班约罗被这一时期的内部政治动荡所削弱,在18世纪逐渐丧失疆域。不过,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之后,它又有了一段复兴时期。[22]在南边,坦噶尼喀湖北部一片极度肥沃、水分充足的山丘上,有卢旺达和布隆迪王国,它们也同样高度军事化,但卢旺达更为成功一些,它在18世纪和19世纪中强力扩张。[23]当然,有着不同的政治体系:东部的中央集权军国主义的布干达,是一些小封邑组成的联盟,称为“索加”(Soga);同样,在布干达和班约罗以北,则是一些更小的、常常是“非国家”的社会,这里的民族生活于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扩张性的霸权政体之间的流动边界上。[24]
英文版原书页码:58
在19世纪,这些国家之间的来往是既有战争又有贸易。例如,布干达与邻国的关系就是实用主义的:有时用贸易和经济影响,有时则使用武力,因为它想建立一个既是疆域的,同时又是“非正式”的帝国。[25]尽管冲突时有发生,但布干达依赖着与班约罗、东边的索加、西边的畜牧国家,以及南边的一系列较小国家和社会的健康的经济关系。然而,这一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却变得更加不稳定,更加紧张,并随着朝向海岸的长途贸易的扩张而在整体上更加暴力——这个贸易网络由桑给巴尔引导。对贸易及其利润的控制,越来越支配着湖泊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贸易本身如同在大西洋非洲一样,从19世纪40年代之后就带来了重要的社会和政治效应。上面提到的国家,绝大多数都尽力参与到贸易中去,只有卢旺达和布隆迪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抵挡住了这种诱惑,并由于这种自我孤立、敌视一切外来者而使自己在当时声誉很高。
如果湖泊地区一些最值得注意的发展涉及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和领土国家的优势,那么,它们的反面也就出现在中东部非洲的其他地区。在现在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一带,19世纪中期之前,很少有类似湖泊地区那种中央集权国家的出现,甚至种族身份都很脆弱,此时仍处在进化之中。这片广阔区域的大部分地区,土地贫瘠,雨水没有保证,因此农业生产十分困难和不稳定。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各个社群仍进行着对移居土地的争夺。与湖泊地区相比,这里的人口密度低,并且定居地趋向散落,不同于布干达和班约罗地区——在那里,城镇模式在1800年前很早就出现了,所以,这里许多地方缺少成熟国家形成的条件。人们倾向于生活在小群体之中,当土地变得贫瘠或者是出现了政治冲突,他们就易于迁移。所以,18世纪和19世纪的坦桑尼亚出现了一些小酋长,他们灵活善变,特点就是持续的变化。
尽管如此,19世纪出现了新的压力,海岸贸易网络向内陆扩张,其结果就是新形式的政治组织在许多社会中出现,以迎接新的挑战并从新机遇中获益。新的领导者也出现了,通常是军事领导者,拥有比以往领导者大得多的个人力量,他们既塑造同时又利用着新的结构。这在尼亚姆韦齐人和金布人中最为明显。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肯尼亚,这里同样在19世纪以前没有形成国家。在肯尼亚内陆(以及坦桑尼亚北部)的尼罗河游牧者中,包括马赛人,人丁年龄管理的组织比任何中央集权的政治控制或人格化的层级体系都要重要。与尼罗河游牧者共存的,还有一些较小的农业社群,尤其是卡姆巴人和基库尤人,他们和马赛人争夺土地和水源,但也同他们联姻、交易以及从文化上得到借鉴。[26]随着19世纪的推移,也有一些社会发生了坦桑尼亚出现的那些变化,新形式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在更强大、更为中央集权的领导体系下出现。如尼亚姆韦齐人一样,卡姆巴人也变成了全球贸易中的积极参与者。
英文版原书页码:59
在尼亚姆韦齐人身上,本地创业和身份流动的主题都体现得十分明显。在贸易和政治活跃的19世纪中期以前,他们并不作为一个“民族”存在。就文化和语言而言,这些旱地的种粮农民是一个松散关联的群体,生活在西部和北部坦桑尼亚,后来开始向更远处的原野迁移,并从增长中的贸易机会里获益。对于海岸和海岸附近的人来说,他们来自西部,因此成为“新月民族”。[27]随着19世纪的来临,尼亚姆韦齐人已经开发出商道,将维多利亚湖北端的布干达、南边的卡丹加以及海岸的桑给巴尔联结起来。他们一直控制着这个贸易网络,直到19世纪中期。如同上文讲到过的,到19世纪中期时,海岸商人就开始带着自己的商队朝内陆渗透了。许多尼亚姆韦齐人成为富有的阿拉伯人和印度商人的运夫,但与这些新来者的冲突也在所难免,尤其当进入内陆的大批海岸商队使当地社群的粮食供应变得紧张时。到了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地方首领要在那些商道穿越的疆域上征收关税,这也引发了对抗。
随着冲突的扩大,海岸商人就越来越寻求介入尼亚姆韦齐的政治。由于这些政体已是支离破碎,他们的介入颇为直接,支持一个部族去对抗另一个,或者利用那些在政治上不满的人,那些人太愿意接受这种武器相对先进的支持者了。靠着拥有武器和商业利益的诱惑,阿拉伯人介入首领间的纷争,开始在酋长国中行使相当大的权力。恩扬耶姆比的例子就显示了这个过程。它位于湖区与海岸之间的主要通道上,19世纪60年代早期这里发生的内战,就出现了阿拉伯人的强硬干涉,这些商人兼探险家先是支持一方首领,然后是另一方,以获取最好的贸易安排。这个阿拉伯社群能够确保对塔勃拉的控制,它开始越来越像一个军事要塞,尤其当贸易变化带来社会政治瓦解与重建,引发了地区战争时,这在19世纪70年代变得更为剧烈。[28]
英文版原书页码:60
与此同时,一个来自南方的暴力新因素开始进入这一地区,这指的是南部非洲的政治—军事事件所引发的深远影响,我们将在下一章介绍。到19世纪50年代,逃离南边祖鲁革命的恩戈尼人群体,渗透到现在的坦桑尼亚地区,带来了毁坏和战争以及国家模式上的转变。他们在大片地区进行袭击和掠夺,以抢劫为生,尽管几年之后也有些人定居稳定下来。比如,乌吉吉在50年代被袭击,而在60年代和70年代,恩戈尼人则从不同的方向穿越坦桑尼亚中部。有一点值得注意,尽管“恩戈尼”这一词通常被用来形容这些群体,但到了50年代和60年代,他们已经是各个被吸纳和被征服的民族的融合,具有恩戈尼的军事精神。有些族群在恩戈尼接近时逃散了,但其他的族群却被它吸纳,有些族群为了生存则复制了恩戈尼的模式,结果变得如同这些移民一样军事化。在这一地区,恩戈尼和它的效仿者引发了一场政治结构和军事化的革命,而此时贸易和社会变化的新力量也从海岸进入到这一地区,显示为暴力的改变力量。由此而来的那些改变,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前后,常常伴随着暴力。
不断升级的暴力和四处蔓延的不安全感,导致了绝望、吸食大麻、高度武装的成群年轻人四处游荡,到处掠抢和冒险,这又使得暴力和不安全感进一步加剧。这大概就是19世纪后半期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了。这些年轻人是社会、政治和经济变化的原因和结果,是旧有秩序垮塌和新秩序重建的征兆。这些人后来被普遍称作“鲁加鲁加”(ruga ruga),但这是一个有问题的用语,因为它指年轻未婚且“职业”的士兵,所以使用此词就显得过分严厉了。“鲁加鲁加”可能是轻罪的罪犯,靠在丛林中抢掠为生,也可能作为雇佣兵依附于贸易车队或者是充当海岸商人的随从。重要的是,他们构成了新出现的军事国家的支柱,这些国家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控制了内陆的一些地区。[29]
这些新国家中最为成功的一个,由尼亚姆韦齐首领米拉姆伯建立。生于1840年左右的米拉姆伯,青年时期做过前往海岸处的商队的运夫,后来继任了塔勃拉西北部的一个小首领。他将这个地方与另一个地方合并,在这个过程中剥夺了其兄的权利要求,建起一支“鲁加鲁加”军队,用它来扩展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基础。几乎可以肯定,这至少是部分受到了恩戈尼人的启发。从60年代末起,他用武力合并了周围的酋长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以城镇和城镇周边的“乌拉姆勃”(Urambo)地区作为中心。他还控制了北部湖泊地区的商道,搜集作为贡品的象牙和牲畜,并利用自己日益增长的贸易力量来收集武器。米拉姆伯是个禀赋异常之人,自己创造了这个国家,它控制着恩扬耶姆比、乌吉吉和维多利亚湖之间的三角地带。他常常亲自带领自己的军队,其雄心似乎是要统一内陆。在这个意义上,尽管他的暴力对于外来者来说常常与那个时代普遍的无法无天相同,却是建设性和创造性的。他相信这几十个小酋长国要被几个强大有力的国家取代,他的国家就是其中一个,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对抗阿拉伯商人、桑给巴尔苏丹以及后来出现在海岸处的欧洲人,对抗这些逐渐增长的力量。为此,他寻求与这一地区其他主要角色的联盟,尤其是布干达的穆特萨,他本身的存在就是对恩扬耶姆比的阿拉伯人的一种威胁,在7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和80年代早期都在与阿拉伯人作战。然而,米拉姆伯“帝国”的力量同时也是它最大的弱点,这就是它过分依赖米拉姆伯本人。当他于1884年末去世后,缺乏内部凝聚力的问题就让他的继任者姆帕杜沙罗无法处理。到80年代末,在德国人入侵前夕,这个国家已经基本瓦解,如同它迅速建立一样迅速地消失了。[30]
英文版原书页码:61
虽然米拉姆伯的事业很辉煌,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即使他对东非政治前景的独特观念或许可以被认为是唯一的。尼亚姆韦齐的另一位领袖姆西里,于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坦噶尼喀湖西南建立了一个贸易和军事强国加朗岗扎(Garenganze),跨越了连接东非与中南部非洲的贸易网络。在米拉姆伯的东南边,金布人中的恩扬古耶马韦(Nyungu-ya-Mawe),以几乎相同的方式——名声更大的同时代人所用的那些方式,开创了一个松散的霸权国家。[31]这些国家都是创新的,富有活力,以暴力来捕捉这个时代的机遇。然而,如同依靠政治创造性一样,它们也依靠无法无天,这就导致了它们内在的不稳定。帮助这些国家建立的那些力量——特别是那些能够也愿意反对前代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年轻一代,受一系列社会、政治和经济渴望驱使的年轻一代,也成为了使得这些新国家长远而言不能持续的力量。领袖个人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得到巨大的忠诚,但要创造稳定的国家体系,使更广的族群尽心投入,这就问题多多了。尽管米拉姆伯试图使自己的战争载入史册,为乌拉姆勃赢得更深厚的政治遗产,[32]但最终还是未能做到比如沙卡为祖鲁所做到的那样。无论如何,这些新国家的存在价值体现了贸易自由和军事冒险,尽管这两者没有一个能与欧洲霸权相抗衡。然而,非洲人参与到全球贸易和试图创建新的政治结构来引导这些力量的活力,预示了殖民统治下的事态发展。

国家创建者:尼亚姆韦齐的米拉姆伯,19世纪80年代初期。
来源:根据伦敦传教协会/世界传道理事会文档复制。
当新的非洲国家出现时,海岸商人正渗透到坦噶尼喀湖以远,进入东刚果。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他们靠着在雨林大片地区的贸易和抢掠,创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对象牙和奴隶的追逐,导致了广泛的破坏,而阿拉伯人则对那些被扰乱的社群进行抢夺,并建立起由武装奴隶和随从组成的私人军队。在这个过程中,削弱了现有的政权资源。坦噶尼喀湖西部地区深深陷入暴力之中,尽管掠夺混战中的最强者也强行施加了某种程度的秩序。这就是艾哈迈德·本·穆罕默德,他被称作“噼啪噼啪”。“噼啪噼啪”是那个时代冷酷商队商人的典型代表。1830年左右,他出生于桑给巴尔一个阿拉伯—非洲家庭,60年代生活在塔勃拉,70年代搬到刚果东部盛产象牙的特特拉(Tetela)地区。他创立了一个可观的势力范围,这靠的是暴力和运到东边的桑给巴尔的满载象牙的商队,后者要穿过与他通常关系良好的米拉姆伯的疆域。“噼啪噼啪”靠着贸易和武力变得富有,但在比利时瓜分刚果时被削弱,他从这里退回到了桑给巴尔。[33]
英文版原书页码:63
“噼啪噼啪”在那些缺乏中央集权大国的地区运作,所以就能够把自己强加于人,让那些社会屈从于他的意愿。不过,他对米拉姆伯的尊敬态度也表明了他与较强大的政体打交道时相当谨慎。在这一区域的其他地方,阿拉伯商人与那些在恩扬耶姆比或东部刚果的同行有着很不一样的经历。在60年代的肯尼亚内陆,马赛人、基库尤人和南迪人都成功地抵御了阿拉伯商队的渗透,当时阿拉伯商人试图绕过卡姆巴中间商。内陆可怕的马赛人的守旧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而那些想要挫败斯瓦希里竞争对手的非洲商人又对此进行固化。[34]在维多利亚湖一带,阿拉伯商人在卡拉格韦(Karagwe)能够发挥一定的政治影响,但在湖的北端,他们面对的是布干达王国——他们在1844年首次抵达这个王国。在这里,他们的贸易做得很成功,但按照干达(Ganda)的通常规矩,他们被干达当局严密监控着,只能在王国都城活动,在这里他们有一个居住区。他们一般不被允许到布干达国内或国外去活动,如果被允许,也会有干达护卫陪同他们。布干达这一时代的两位国王苏纳(约1830—1857)和穆特萨(1857—1884),都从事以奴隶和象牙来换取枪支、布料和其他商品的有利贸易,这在布干达那种竞争性的重商和军事化文化中被高度推崇。进口的棉布改变了上层阶级的时尚,同时也象征着改变之中的社会经济渴望。然而,枪支则很快在军事建设中发挥了作用,穆特萨尤其对武器的潜力乐观。在控制维多利亚湖地区贸易上的争夺,促使干达人使用军事手段来保护商业利益。对于军队本身而言,获取奴隶也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行动。这就使得布干达王国与它的邻国如班约罗、布索加(Busoga)以及西边其他国家发生冲突。[35]
如同尼亚姆韦齐人,干达人在抓住贸易机遇上也是积极且富有侵略性的。不过,到19世纪70年代,这支军队在疆域上的过分野心使得它开始走过头了。干达人的尚武精神被王国中心的政治紧张所削弱,在那里代际冲突部分体现为对不同外来信仰的效忠之上。还有证据表明,越来越多缺乏训练的士兵使用武器,正在削弱这个王国的军事能力。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以后,干达人想通过建立一支可以从北到南横跨大湖的船队来支配湖区贸易。到70年代,布干达已经成为这一地区主要的奴隶出口者之一,而且它的“海军”是一种可观的创举。然而,这个王国并未如穆特萨显然希望的那样,使自己在对外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变得强大。到了80年代末,穆特萨的王位已由姆万加继承,他是一个缺乏经验的年轻人,而且此时布干达与复苏的班约罗之间的冲突正在加剧,内部也有着宗教和政治冲突。[36]最终,干达人与英国人结为同盟,一起对周围地区进行殖民镇压,“乌干达”这个名称后被用于这片未来的殖民疆域。
英文版原书页码:64

布干达的国王穆特萨及其大臣,19世纪70年代后期。
来源:世界史档案/UIG取自格蒂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