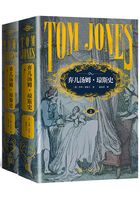
第一章
仅占五页。
有些无稽之谈的传奇,满纸妖魔鬼怪——那并非造化自然的产儿,而只是头脑昏乱的产物——惹得一位卓越不群的批评家说,这类东西,该送到点心铺,专供铺子的老板使用 ;我们所写,既全属真实,则与此有别。另一方面,有一类历史,就惹得一位声誉卓著的诗人
;我们所写,既全属真实,则与此有别。另一方面,有一类历史,就惹得一位声誉卓著的诗人![声誉卓著的诗人,指蒲伯而言,后面那两行诗,引自他的《椎士录》(1728年版)第3卷第205—206行。说他几乎认为供酒厂老板赚钱而写书,也是这句诗推演出来的。(《椎士录》在蒲伯生前即有四版,增删、改动很大;此处这两行,只于异文校注本中见之。此注据特维克纳姆[Twickenham]版本。)](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469CF6/147112298056675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36686177-0stLTdOoQNy36S8KcTMkJp0iWJJmZPxo-0-ea702c6d12b6b8d965e178600ad8ac5f) ,几乎要认为,也是出于同样的打算而写的,只为了供酒厂老板赚钱;因为要读这类史书的时候,总得伴之以大碗好酒才成。正是:
,几乎要认为,也是出于同样的打算而写的,只为了供酒厂老板赚钱;因为要读这类史书的时候,总得伴之以大碗好酒才成。正是:
史书里令人悲歌慷慨的故事,
 累累,
累累,
读起来必须伴以曲糵 ,才消得胸中块垒。
,才消得胸中块垒。
我们所写要避免和这类历史有任何相似。
本来,如果说酒能启发作者的文思(不但启发文思,而且启发灵感;我们如果认为勃特勒 的看法不错,就得这样说,因为他把灵感的启发,归于饮酒的作用),那就得说,酒也能启发读者的情趣;因为作者写一部书,和读者读一部书,应该持同样的精神,抱同样的态度——都得跟饮酒一样,啜其醇醪,弃其糟粕。
的看法不错,就得这样说,因为他把灵感的启发,归于饮酒的作用),那就得说,酒也能启发读者的情趣;因为作者写一部书,和读者读一部书,应该持同样的精神,抱同样的态度——都得跟饮酒一样,啜其醇醪,弃其糟粕。 可能由于这个缘故,所以《赫娄斯洛姆勃》的著名作者
可能由于这个缘故,所以《赫娄斯洛姆勃》的著名作者 ,才对一位学问渊博的主教说,主教大人所以对他之所作,不能品尝其精妙,只是因为,主教大人读那本书的时候,手里没拿小提琴,而他自己写那本书的时候,则小提琴从未离手。
,才对一位学问渊博的主教说,主教大人所以对他之所作,不能品尝其精妙,只是因为,主教大人读那本书的时候,手里没拿小提琴,而他自己写那本书的时候,则小提琴从未离手。
情理既是这样,因此,为了使我们的著作,不要让人家比作这类历史的写作那样,有乞灵于曲糵之嫌,我们在全书里,只要遇到机会,就点缀上一些譬喻比拟的词句、绘影绘声的描写,和一切诗情歌意的藻饰。这类藻饰,说实在的,我们就打算用来取前述曲糵的地位而代之,一旦遇到睡魔要暗袭读者的时候,就用它们使读者的脑筋清醒一下;因为一部长篇巨制的读者,也和一部长篇巨制的作者一样,都是非常容易受到睡魔的明侵暗袭的。假使没有这类点缀穿插,那么,一部平铺直叙的故事书,即便顶娓娓动听,读起来也绝难使人免于为睡魔所困;因为除了一直聚精会神、永远警醒不寐(据荷马说,只有一个朱庇特,能做到这一步 ),没有别的本领,能使人读成本成本的报纸而不生疲倦。
),没有别的本领,能使人读成本成本的报纸而不生疲倦。

琼斯于媢丽的屋子中发现斯侩厄。(第五卷第五章)
我们在书里点缀这种藻饰,都各有其时令,至于这种时令选择得当与不当,我们完全听从读者来下评判。但是,如果我说,要用这种点缀,莫妙于现在这个时候,那我敢保,不会有人反对;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导引一位重要角色,登台上场,这位角色,并非别个,乃是这部亦文亦武、亦散文亦诗歌、亦历史亦小说的著作里那位女主人公。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在这儿,把大自然所呈现的千种丰姿、万方仪态,尽量挹揽采撷,灌输于读者的心中,以使他们思想上做好准备,来迎接那位最重要的角色。对于这种办法,我们可以援引许多先例来解释。首先,这本是我们的悲剧诗人所熟知、所常用的手法;在他们的主要角色上演之先,他们几乎没有不预为他们的观念作好思想准备的。
所以,威武的主角要登台,先得鼓号齐鸣,来一阵“打通儿”,这样,观众才能抖擞起勇武的精神来,才能听起夸大浮词、狂诞虚语 ,习之若素,不觉刺耳;本来这种浮词虚语,如果洛克先生说的那位盲人,把它也比作号角之声
,习之若素,不觉刺耳;本来这种浮词虚语,如果洛克先生说的那位盲人,把它也比作号角之声 ,那倒并不能算大错而特错。又如,在双双情侣要上场的时候,往往有柔和旖旎的音乐,作他们的先导,以引起观众温柔缠绵的情思,同时使观众甜酣畅适,如入梦乡;他们大致就是在这样的梦境迷离之中,观赏领略随后而来的剧中情景的。
,那倒并不能算大错而特错。又如,在双双情侣要上场的时候,往往有柔和旖旎的音乐,作他们的先导,以引起观众温柔缠绵的情思,同时使观众甜酣畅适,如入梦乡;他们大致就是在这样的梦境迷离之中,观赏领略随后而来的剧中情景的。
而且不但是诗人,即便诗人的提调——剧院的经理,好像也懂得这个诀窍;因为,除了前面所说的击鼓吹号等等,以预示主角要登台而外,通常还有大队人夫,亦即六七人组成的布景队,做他们的先驱。这班人对主角登场有多重要,从下面这件舞台琐闻来看,就可以得出结论。
扮庇洛斯王的演员,注3正在剧院隔壁一家酒馆进餐,有人喊他,叫他出台。这位主角,既舍不得扔下他那盘羊臀尖,又不愿意让观众等候,而惹翻了他那位同伙——剧院经理维勒克斯先生, 所以预先就把那帮给他打前站的人,都买通了,叫他们都躲了起来。这样一来,尽管维勒克斯先生咆哮如雷,大叫“给庇洛斯王铺排开路的木匠,
所以预先就把那帮给他打前站的人,都买通了,叫他们都躲了起来。这样一来,尽管维勒克斯先生咆哮如雷,大叫“给庇洛斯王铺排开路的木匠, 都跑到哪儿去了?”那位国王,还是不动声色地安享他的羊臀尖,而观众不管怎么急不能耐,也只好在他还没出场的时候,听听音乐,聊以解闷。
都跑到哪儿去了?”那位国王,还是不动声色地安享他的羊臀尖,而观众不管怎么急不能耐,也只好在他还没出场的时候,听听音乐,聊以解闷。
注3庇洛斯(Pyrrhus,希腊文Π ,公元前318—前272),在历史上为艾派厄罗斯(Epirus)国王,以善战著。此处则为剧中角色。此剧为《痛苦的母亲》(The Distressed Mother),本是拉辛(Jean Racine,1639—1690)的《昂得罗玛格》(Andromaque),由费利浦斯(Ambrose Philips,1675? —1749)译编,其中男主角为庇洛斯。于1712年初次上演。这儿这个演员是布斯(Barton Booth,1681—1733),英国悲剧演员。这个琐闻,就是他的故事。
,公元前318—前272),在历史上为艾派厄罗斯(Epirus)国王,以善战著。此处则为剧中角色。此剧为《痛苦的母亲》(The Distressed Mother),本是拉辛(Jean Racine,1639—1690)的《昂得罗玛格》(Andromaque),由费利浦斯(Ambrose Philips,1675? —1749)译编,其中男主角为庇洛斯。于1712年初次上演。这儿这个演员是布斯(Barton Booth,1681—1733),英国悲剧演员。这个琐闻,就是他的故事。
说老实话,我颇怀疑,那班政客,鼻子总是很尖的,会一点儿都嗅不出这种办法的妙用来?我深信不疑,那位赫然威严的治安大人——市长老爷,每年在任上的一年期间,所以能得到那样的敬仰尊荣,大部分都是由于他的花车前面,摆列了各式各样的盛大行列 。不但这样,我还得坦白承认,连我这样的人,本来并不特别容易看到外观表相,就心迷魂夺,但是见了从者呵道、卫士前遮,也不由得大为咨嗟赞叹。在一个行列里,如果一个人独自居后,昂首阔步,而其余的人,都只是充当他的马前卒、先行官,那看到他,比在平常的情况下看到他,总要觉得他更威风凛凛。不过有一样事例,却和我的心意,完全不相悖谬,那就是下面说的这一种习俗。原来举行加冕重典之时,堂堂显贵,还未依序列队,鱼贯入场,就先派女子一名,手提花篮,于举行仪式之先,在礼堂里遍撒鲜花。古代的人,毫无疑问,一定要呼求司花女神,来担任这番美差;同时,他们的僧侣或者政客,也不要费什么事,就能使人完全相信,司花女神真个临世降凡,虽然实际装扮这个角色、执行这个任务的,不过只是一个普通的凡间女子。但是我们却没有打算这样欺骗读者的意思,因此那般反对古代神道设教的人们,如果高兴的话,可以把我们的司花女神,换而为前面所说的提篮女子。简而言之,我们的意图,只是想要用高超卓越的文笔,和其他一切足使读者提高敬慕之心的情境,尽我们所有的一切庄严肃穆,把我们的女主人公引导上场。我们这位女主人公的形象,既是纯由模拟自然而来,其应受爱慕,自不待言;但是,如果我们不是确实敢保,在我们那些美貌的女同胞中间,可以找到许多位,都配接受任何强烈的爱情,都合乎我们笔下所要描绘的任何完美女性形象,那我们的女主人公,不论多么应受爱慕,我们为了某些缘故,也要奉告我们的读者之中那些稍谙风情的诸位,不要再读下去。
。不但这样,我还得坦白承认,连我这样的人,本来并不特别容易看到外观表相,就心迷魂夺,但是见了从者呵道、卫士前遮,也不由得大为咨嗟赞叹。在一个行列里,如果一个人独自居后,昂首阔步,而其余的人,都只是充当他的马前卒、先行官,那看到他,比在平常的情况下看到他,总要觉得他更威风凛凛。不过有一样事例,却和我的心意,完全不相悖谬,那就是下面说的这一种习俗。原来举行加冕重典之时,堂堂显贵,还未依序列队,鱼贯入场,就先派女子一名,手提花篮,于举行仪式之先,在礼堂里遍撒鲜花。古代的人,毫无疑问,一定要呼求司花女神,来担任这番美差;同时,他们的僧侣或者政客,也不要费什么事,就能使人完全相信,司花女神真个临世降凡,虽然实际装扮这个角色、执行这个任务的,不过只是一个普通的凡间女子。但是我们却没有打算这样欺骗读者的意思,因此那般反对古代神道设教的人们,如果高兴的话,可以把我们的司花女神,换而为前面所说的提篮女子。简而言之,我们的意图,只是想要用高超卓越的文笔,和其他一切足使读者提高敬慕之心的情境,尽我们所有的一切庄严肃穆,把我们的女主人公引导上场。我们这位女主人公的形象,既是纯由模拟自然而来,其应受爱慕,自不待言;但是,如果我们不是确实敢保,在我们那些美貌的女同胞中间,可以找到许多位,都配接受任何强烈的爱情,都合乎我们笔下所要描绘的任何完美女性形象,那我们的女主人公,不论多么应受爱慕,我们为了某些缘故,也要奉告我们的读者之中那些稍谙风情的诸位,不要再读下去。
现在,我们不再喋喋老谈引言,而往下叙说次一章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