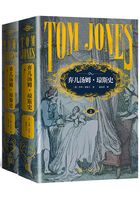
第六章
用明喻介绍玳波萝阿姨在区上出现。简单叙述珍妮·琼斯,兼及年轻女子想求学问所遇之困难、挫折。
玳波萝阿姨体会主人的意愿,把婴孩安置好了,现在正准备到假定窝藏婴儿的妈那些人家去访问侦查。
一只众鸟畏惧的猛禽鹞鹰,一下为小小羽畜所发现,看见它在天空翱翔,在它们头上盘旋,那时候,所有相偎相依的鸽子 以及每只无害无辜的小鸟,就忙忙碌碌地把警报遥传,胆战心惊地飞到它们的藏身之处。鹞鹰就拊翼太空而自傲,呈威奋勇而自得,心里把打算要做的恶事一意琢磨。
以及每只无害无辜的小鸟,就忙忙碌碌地把警报遥传,胆战心惊地飞到它们的藏身之处。鹞鹰就拊翼太空而自傲,呈威奋勇而自得,心里把打算要做的恶事一意琢磨。
玳波萝阿姨的出现,就和这种鹞鹰完全相同。她走到近前的消息在街上传来的时候,所有的居民都手颤足摇地跑回了自己的家里,每家主妇都把一颗心提溜着,唯恐她的光临落到自己头上。她威风凛凛地高视阔步走过田间,把俯临一切的脑袋高仰空中,一心充满了炫耀显赫的自骄,心里盘算,怎样才能把打算好了的侦查工作办得成功。
精明聪慧的读者,不会看了这个明喻就设想,认为这些可怜的人,明白维勒钦阿姨所以光临,究竟抱着什么阴谋诡计。不过因为这个明喻的优美,也许得过一百年,身居睡乡,无人唤醒,一直等到将来有的注释家从事诠释这部书的时候才能清楚,所以我认为,我应该在这儿稍助读者一臂之力。
因为如此,所以我的意思要指明一下,既是鹞鹰生来就以吞噬小小的鸟儿为能事,所以,像维勒钦阿姨这样一类的人,就生来以鄙视欺骗,压迫虐待小小的人物为事。实在说起来,这样的人就用这样的方式,取得补偿,以抵消他们对在他们之上的人所尽的极端谄媚和恭顺。因为甘心为奴和工于献媚的人,既向在他们之上的人供奉献纳,那他们对在他们之下的人就得摊派勒索;天下的事,还有比这个更合情合理的吗?
玳波萝阿姨有的时候,得对白蕊姞小姐非常特别地卑躬屈节,因而把她天生的脾气惹得有些烦闷苦恼,每逢遇到这种时候,她通常总是跑到这些人们中间,大大发泄一通,以使脾气变得优婉娴雅,使苦恼烦闷得到洗涤清涮(这是比喻)。因为有这种原因,所以她不论走到哪儿,都绝对不受欢迎,说实在的,所有的人,普遍地对她无不又怕又恨。
她来到这个地方,马上进了一位年事垂老的主妇家里。这个女人,由于运气好,有幸在尊容方面和芳龄方面都和她有相似之处,所以她对这个人比对其他任何人,一般都较垂青。她对这位主妇把发生的事儿,还有那天早晨她到那儿去的用意,全都说了。于是她们两个,紧跟着就把住在这一带好几个年轻的女人都是什么品行,细细地计议、考查了一番。最后她们认定,一个叫珍妮·琼斯的人最为可疑,因此她们一致认为,这个事儿百分之百是她干的。
这个珍妮·琼斯,不论面貌身段,都不能说非常顺眼;但是老天却因为她缺乏丽姿秀色,给了她另一种优点作为补偿;这种优点,据年龄已经达到完全成熟之期、判断可以作准的女人看来,还更可贵,因为她生来就有一份非常过人的悟性。这种天赋,再加上好学,越发使她大有进益。她有好几年工夫,都在一位塾师家里做女仆,这位塾师,发现这个女孩子天分聪明伶俐,又特别喜欢学习——因为只要她一有闲工夫,就有人看见她把学童念的课本拿着阅读——就不惮烦劳,或者说犯了傻气,不管读者高兴怎样说都成,一意教她,一直把她教得对于拉丁文的掌握,完全达到合格的程度;她也许称得起和现代绝大多数的贵家子弟是一样的学者。但是这种长处,也和大多数突出过人的长处一样,也带来了一些小小的麻烦;因为一个年轻的女人,既然有了这样的才情学问,就要觉得,和那班命运使之与她身份相等、教育却使之比她身份低下的人交接往来,没有意味,这是不足为奇的;那么珍妮的优越,加上随着优越必然而来的行为,会在其余那些女孩子中间,引起一些对她小小的嫉妒或恶感,更无可诧异。这种种感情,自从她不当女仆回到家里以后,一直在她那些邻居的胸中,暗暗燃起一把无名怒火。
不过,她们这种嫉妒,外面却隐忍不露,一直顶到有一个礼拜日,可怜的珍妮穿着一件新绸子长袍,戴着一顶绣花边的便帽,还有其他和这种服饰配衬的装点,在大众面前显露,惹得人人都诧异,招得所有这方近左右的年轻女人都恼怒。
这种愤火,原先只在胚胎状态中,现在都猛然破壳而出。原先珍妮因为有点儿学问,骄傲自得,她的邻居固然连一个都没有能友善为怀,满足她这种骄傲仿佛要求的荣耀;现在,她叫华服丽饰一摆弄,所得到的更不是尊敬和崇拜,而是仇恨和辱骂。整个区上的人,都到处扬言,说这类东西,绝不是由正路来的,当父母的,就不但不愿意他们的女儿有这种东西,反倒因为他们的孩子没有这种东西而自庆自幸。
大概就是因为有这种情况,所以那位好心眼儿的主妇,才对维勒钦阿姨点着名儿把这个可怜的女孩子头一个提了出来;不过还有另一种情况,使维勒钦阿姨的疑心得到证实:因为珍妮近来常常在奥维资先生的宅子里走动。原来白蕊姞小姐忽然得了一场非常厉害的重病,她曾当护士,伺候过病人;有好多夜晚,都通宵达旦,陪伴过病人;除此而外,维勒钦阿姨还正在奥维资先生回来的头一天,亲眼看见她在宅里进进出出。不过这位老成持重的阿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因为那样而就起了疑心;因为,像她说的那样,她认为珍妮是个安顿稳重的女孩子(其实她并不十分了解她),总是很看得起她。她只疑心那些轻薄放浪的淫娃荡妇,她们老是挺神气的,因为,一点儿不错,她们认为自己长得漂亮标致。
玳波萝阿姨现在传珍妮,叫她当面来见,珍妮马上就来了。玳波萝阿姨于是摆出一副法官的庄严面孔,并且比法官还更严厉的态度,用以下的字眼儿,开始她的训词:“你这个不顾羞耻的娼妇,你好大胆。”她就用这一类的辞藻说下去,说的口气,与其说对犯人提出起诉,还不如说对犯人宣布判决。
虽然玳波萝阿姨根据前面指出来的理由,满心认为珍妮犯了罪,但是奥维资先生却很可能需要更加有力的证据,才能判她有罪。不过这女孩子却使她的控诉者省去一切麻烦,干脆承认了她被控诉的全部事实。
这番承认,虽然由外表上看来,是以悔恨之词出之的,却一点儿也没能使玳波萝阿姨心软;她现在二次对罪人下了判决,用的词句,比以前更恶毒。这阵儿看热闹的人聚得很多了,他们也同样地不顾她的悔恨之词,只一味地对罪人口诛声讨。他们中间有好多的人大声喊着说,他们早就想到了,这个小娘儿们的绸子长袍会有什么下场;另外有的人就挖苦讥笑她的学问。所有在场的妇女,没有一个想不出几句话来,表示她对可怜的珍妮深恶痛绝的。珍妮呢,对于所有这些辱骂,一概老老实实地忍受,唯一的例外,是对一个女人的恶詈。这个女人对她的形貌进行了攻击,把鼻子一嗤,嘴里说,“这个男的,一定口味太高了,才把绸子长袍送给这样一个娼妇!”珍妮对于这个妇人的反击,异常辛辣,一个有辨别是非之力的人,看到她对于攻击她的贞操那些话,一概默默忍受,而对于这一点却进行这样尖刻的反击,一定要觉得诧异。这也许是因为她的忍耐力已经衰竭了吧;这种美德,叫它尽力过分,本来就很容易疲惫的嘛。
玳波萝阿姨在她这番侦查中,既然获得意想不到的成绩,就大张旗鼓地凯旋,并且在指定的时间,向奥维资先生如实汇报。奥维资先生听了这一番话,大吃一惊。因为他早就听说这个女孩子非常有才气,非常有长进了,本来还打算外带着一份小小的圣俸 把她嫁给邻区一个副牧师;因此,这一回他觉得难过的程度,至少赶上了玳波萝阿姨显得满意的程度。这让许多读者看起来,也许更合情理。
把她嫁给邻区一个副牧师;因此,这一回他觉得难过的程度,至少赶上了玳波萝阿姨显得满意的程度。这让许多读者看起来,也许更合情理。
白蕊姞小姐自庆天佑,说在她那一方面,从此以后再也不能对任何妇女抱有好感了。因为珍妮在这件事发生以前,也很有幸,是白蕊姞小姐极为垂青的人。
那位审慎谨饬的管家婆又受派遣,去把那个不幸的罪人,带到奥维资先生面前,倒不是为的好把她送到矫正所,像一些人希望和全部人指望的那样,而是为的好给她一番有益心神的警告和训诫。这是那般对这类教诲式的写作能品评滋味的读者,在下一章里可以读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