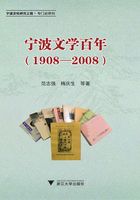
第一节 20世纪30年代的诗歌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代新诗,沿着20年代开创的“大众化”与“贵族化”两种不同倾向继续发展,“出现了以殷夫为前驱、蒲风为代表的中国诗歌会诗人群,和以徐志摩、陈家梦为代表的后期新月派,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群两大派别相互竞争的局面” 。
。
中国诗歌会于1932年9月在上海成立,是左联领导下的一个群众性诗歌团体,发起人为穆木天、蒲风、杨骚、任钧等。他们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诗歌为武器,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在艺术形式上提倡“诗歌大众化”,并出版过“歌谣专号”,刊登以民歌、小调、鼓词、儿歌等形式写作的新诗。1935年,当抗日斗争成为时代主题时,中国诗歌会的诗人们又提出“国防诗歌”的口号,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并在1937年出版了“国防诗歌丛书”。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该团体停止了活动。中国诗歌会的代表作品有殷夫的《1929年5月1日》,蒲风的《茫茫夜》《六月流火》,穆木天的《在喀林巴岭上》等。
中国诗歌会从一开始就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有着血肉联系,许多诗人都自觉投身革命,用自己的诗歌、行动甚至生命进行斗争。这一点在其前驱诗人殷夫(“左联五烈士”之一)的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而这位才情纵横、铁骨铮铮的诗人正是来自于宁波象山。
同时期,还有另一位曾与鲁迅等人共同创办“朝花社”的宁波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籍诗人——崔真吾。他虽不是中国诗歌会的成员,却同样是“我以我血荐轩辕”,将生命献给了诗歌与革命。
一、东方的微光:殷夫的诗
殷夫(1909—1931),浙江宁波象山县人,原名徐柏庭,学名徐白、徐祖华,笔名有殷夫、白莽、任夫、沙菲、沙洛等。殷夫十三四岁即开始写诗。1928年加入太阳社。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发起人之一。1931年1月17日,他参加党内秘密会议,因叛徒告密,与柔石、冯铿等八人被英租界巡捕逮捕,2月7日晚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附近的荒野里,年仅22岁。

殷夫
殷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继郭沫若、蒋光慈之后,又一位重要的,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的革命诗人。以《血字》和《别了,哥哥》等为代表的“红色鼓动诗”,代表了殷夫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最富特色的政治抒情诗。在短短的创作生涯中,殷夫留下了诗作99首,译诗11首,新中国成立后编印成诗集《孩儿塔》《殷夫选集》《殷夫集》。
20世纪20年代初,许多被革命惊雷唤醒的中国热血青年,以各自不同的爱国心纷纷踏上革命的旅程,殷夫也在其中。战争的隆隆炮声和革命的号召声,形成了巨大而浓重的政治氛围,并且积淀在他们的血液里。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和对革命理想的追求,铸成他们忠诚的品格和神圣的情怀,火热的时代以巨大的精神感召力激发起少年殷夫创造的激情。出生于象山的殷夫本身具有象山人那种搏击与幻灭共存的激越性格,天生聪慧的他从小便有一种超越的心态,不甘心做一个凡夫俗子,他渴望投身到一个伟大的运动中,给自己的生命注入价值,即使运动危险丛生,苦难重重,甚至是要牺牲亲情和爱情,他也义无反顾。
我们可以从收在《孩儿塔》诗集里最早的一组诗《放脚时代的足印》看出,殷夫从少年时代就显露出卓越的诗才。这组诗已经表现出作为一个诗人应具备的各种品质:早熟、敏感、想象丰富、情绪动荡,又有纯熟的语言表达能力。譬如“听不到颂春的欢歌,不如归,不如归……只有杜鹃凄绝的悲啼”。短短几行诗透露出少年诗人对于平凡事物的敏感和想象。这种触景生情、多愁善感的性情,使诗人在青春期刚刚来临之际,不仅像一般孩子那样具有天真的幻想和美丽的憧憬,同时还感到了希望的渺茫:“希望如一颗细的星儿,在灰色远处闪烁着,如鬼火般的飘忽又轻浮,引逗人类走向坟墓”。他在此时也萌发了朦胧的爱情,所以在早期爱情诗也占了他作品的一大部分。殷夫的早期爱情诗,主要表现诗人初恋时的稚气、欣喜和羞涩。“我们同坐在松底溪滩剖心地,我俩密密倾谈。”“我们同数星星笑白云儿多疏懒。”甜蜜天真的情态跃然于纸上。“我记得,我偷偷看你的眼睛阴暗的瞳子传着你的精神。”“我记得,我望望你的面颊瘠瘦的两颐带着憔悴的苍白。”在《我们初次相见》中,他那种矜持忸怩而略带伤感的神情如在目前。诗人小小年纪就有了初恋、接吻、离别等人生体验:“我初见你时,我战栗着,我初接你吻时,我战栗着,如今我们永别了,我也战栗着。”所有这些都是一个诗人不可或缺的基本品格,即使一位无产阶级革命诗人也不例外。
在他创作处女作《放脚时代的足印》时,作者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同那个黑暗的时代中许多探索真理的青年一样,他经历着成长期的彷徨和失望。在他最深刻的佳篇长篇叙事诗《在死神未到之前》中,他在狱中一口气就写下了这首八章的长诗,详尽描述了第一次被捕的始末以及他起伏难平的心情。年少缺乏革命经验的他在第一次被捕时在诗中抒发了自己的一些“阴面”情绪,如起初的恐惧、悲戚之感,对人生、母亲的过于依恋之感,这都和一个成熟的革命者的境界有一定的距离,但这些诗歌更为真实地反映了作为革命者的殷夫和作为诗人的殷夫之间高度同构的关系。狱中的殷夫通过诗歌这种极致抒发个人情感的文学形式来表现他的青春躁动的情感,诗中“阴面”情绪的袒露是十分真实自然的。
从1930年《孩儿塔》之后的作品,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作者在经历了革命的磨炼后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他由一个不成熟的天真的革命者逐渐变得成熟起来,革命的决心也变得更加坚定,他最初的革命冲动和青春躁动转化成了恒定的革命心理,面对死亡,诗人并没因死神即将到来而消沉倒下,他是懂得为阶级的事业献身的——“革命的本身就是牺牲,就是死,就是流血,就是在刀枪下走奔”。他正气凛然,决心从容赴死——“在森严的刑场,我的眼泪不因恐惧而洒淋”“死去!死是最光荣的责任,让血染成一条出路,引导着同志向前进行”。他在死神面前信念依然坚定——“但是朋友,我并不怕死,死于我象一种诱引,我对之不会战栗,我只觉得我的光明愈近!……死在等候着我,和他一起的还有光明”。在诗中活跃的是一个赤热忠诚的革命者的形象。诗中对围观群众的热情呼唤,对叛徒敌人的愤恨斥责,对工农大众的殷切寄望,都反映出诗人自觉清醒的阶级意志和革命意识。所以他的诗一发表就受到革命文学前驱者的赏识和推崇。在殷夫这里,革命是事业,文学是手段,他的审美冲动往往被政治激情所冲淡。当革命高潮到来,他便弃文从政,完全陷入政治中。这一切均源于年轻的他个性气质中对理想世界不舍追求的先天禀赋。
鲁迅在为殷夫《孩儿塔》所作序言中,这样写道:“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思想背景以及地域和家庭的渊源,激越的个人气质基础,在生活和革命道路上的种种体验,共同构成了殷夫诗歌创作风格。殷夫曾在诗集自序《“孩儿塔”上剥蚀的题记》中说:“我的生命,和许多这时代的智识者一样,是一个矛盾和交战的过程,啼、笑、悲、乐、兴奋、幻灭……一串正负的情感,划成我生命的曲线;这曲线在我的诗歌中,显得十分明耀。”从殷夫的这段自白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殷夫,一个去除了革命光环的平凡的殷夫,他的生命曲线正是个人情感与公众情绪相交融的艺术记录。
二、柔美而艳丽:邵洵美的诗
邵洵美(1906—1968),祖籍浙江余姚,出生于上海。原名邵云龙,笔名浩文、郭明、朋史、忙蜂等。诗人,散文家,出版家,翻译家。出版过三部诗集:《天堂与五月》《花一般的罪恶》《诗二十五首》。先后主办、出版过十几种刊物,如《狮吼》《金屋》《新月》《时代画报》《文学时代》《万象》《论语》《时事日报》《自由谭》等。

邵洵美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文坛,邵洵美是当之无愧的风云人物。他出身名门,家财万贯。祖父邵友濂,为晚清重臣。外祖父盛宣怀(亦即其妻盛佩玉的祖父)是中国近代的第一代大实业家。而为他带来更大声誉的是他交游广阔,慷慨大方,经常出手资助文坛友人,斥巨资发展中国的出版事业,人称“小孟尝”。
然而邵洵美本人更看重的是自己的诗人身份。他曾在英国留学,深受英法唯美主义思潮的影响,被誉为“中国的唯美主义诗人”。他的诗多描写都市生活,强调人的感官和欲望,颓废气息浓郁,语言优美细腻,善用象征、暗喻的手法,讲究技巧和形式。我们从他友人对他的评价就可了解他诗作的风格:“邵洵美的诗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气,艳丽如一个应该赞美的艳丽的女人。”(陈梦家语)“以官能的颂歌那样感情写成他的诗集。赞美生,赞美爱,然而显出唯美派人生的享乐,对于现世的夸张的贪恋,对于现世又仍然看到空虚。”(沈从文语)他的颓废诗风在当时即毁誉参半,新中国成立后更是长期遭受冷遇。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他的相关研究才开始缓慢升温。
邵洵美一生对诗的探索,是他对美的追求。
邵洵美早期的诗,取材广泛。《天堂》写了天堂、人间——阴谋、暴虐的上帝,易被诈骗、诱引的奴隶,为了真爱而被罗织罪名的青年男女。罪恶的天堂,那是人间的地狱,是作品给读者的第一印象。《花姊姊》长达300多行,实则只是表现了人生如进屠宰场的牛羊,死如一只蚂蚁;人与人之间只是杀与被杀。但诗人解不开人生的谜,企图从人性善恶抑或环境逼使找原因:他们“为了怕自己死,所以恨别人生”,最终停留在非常皮相、非常一般的层面——“自私”上。
作者的第一本诗集,在长诗艺术上几乎一无可取。《花姊姊》中重复写战场上“杀”“死”各达百行。这里只引写“死”的一段,读者可借此一斑而窥全豹:
死死死!/你死,/他死,/我死,/死死死!
死死死!/你半死,/他半死,/我半死,/死死死!
死死死!/你也死,/他也死,/我也死,/死死死!
一个死,/两个死,/五个死,/十个死,/死死死!
死死死!/五十个死,/一百个死,/一千个死,/一万个死,/死死死!
死死死!/几万个死,/多多少少个死,/死死死!
对重复堆砌的赞美,在新诗中,基本没有超过它的。短诗则大多有点诗意,如《头发》描写颇出色:
啊这北极雪山般白的颊上,
漂来一层淡红芍药色的轻浪;
那眼球眉梢及发髻,
又像水獭休息在岸旁。
诗人对头发线条、着色的描写不失画家的本色,色彩和笔触细腻,描画到位。诗的最后一节,引人无限遐思:
啊情人的头发吓,
在情人心中打着结;
情人在这最短最快的时光吓,
分分秒秒只是去解这无穷的结吧。
这可以理解为,情人的头发有千千结,等待爱人去解开,或者是在相聚的很短的时间里,爱人欣赏她的情意。他的短诗不同于长诗明说,比喻也不是明喻,让读诗的人可以天马行空地随意想象。
邵洵美的早期诗歌模仿波特莱尔等人的痕迹较重,追求新奇艳丽的词句和铿锵的格律,形式上过分雕琢,对肉欲的歌颂缺乏节制,艺术成就不是特别高。例如这首《五月》:“啊欲情的五月又在燃烧,/罪恶在处女的吻中生了;/甜蜜的泪汁总引诱着我,/将颤抖的唇亲她的乳壕。”
他后期的诗歌突破了格律的限制,“转向在诗歌的‘肌理’上用力,注重意象的营造” ,其颓废唯美的艺术风格渐趋成熟,显示出较高的诗才。比如这首《蛇》:
,其颓废唯美的艺术风格渐趋成熟,显示出较高的诗才。比如这首《蛇》:
在宫殿的阶下,在庙宇的瓦上,
你垂下你最柔软的一段,
好像是女人半松的裤带
在等待着男性的颤抖的勇敢,
我不懂你血红的叉分的舌尖
要刺痛我那一边的嘴唇?
他们都准备着了,准备着
在同一时辰里双倍的欢欣!
我忘不了你那捉不住的油滑
磨光了多少重叠的竹节:
我知道了舒服里有伤痛,
我更知道了冰冷还有火炽。
啊,但愿你再把你剩下的一段
来箍我箍不紧的身体,
当钟声偷进云房的纱帐,
温暖爬满了冷宫稀薄的绣被!
苏雪林曾在《颓加荡派的邵洵美》 一文中断语邵洵美的诗:“强烈刺激的要求和决心堕落的精神”,“以情欲的眼观照宇宙一切”以及“生的执着”。苏雪林并将时人对徐志摩的“不确切”批评语赠邵洵美:“情欲的诗歌,具烂熟的颓废的气息”,且说“真是天造地设,不能分毫的移动了”。
一文中断语邵洵美的诗:“强烈刺激的要求和决心堕落的精神”,“以情欲的眼观照宇宙一切”以及“生的执着”。苏雪林并将时人对徐志摩的“不确切”批评语赠邵洵美:“情欲的诗歌,具烂熟的颓废的气息”,且说“真是天造地设,不能分毫的移动了”。
《蛇》状蛇而写女人。四节诗分别书写肉欲需要与肉欲憧憬,后两节则均为回忆与憧憬的交织。粗粗说来,油滑磨光竹节两句为回忆,伤痛、火炽两句及第四节兼写回忆憧憬。诗人摹写的肉欲的胜处就在“双倍的欢欣”:多么绝妙呵,“我不懂你血红的叉分的舌尖/要刺痛我那一边的嘴唇?”“你”的舌尖有叉分(蛇分叉的舌尖类化为女人上下唇),“我”的嘴唇有两瓣,诗人于是妙笔生繁花,一份欢欣作双倍想了。诗中传达的忧伤是不言而喻的。女人油滑,必游刃有余于众多“竹节”之间吧?而这些“竹节”是同时被磨光的。因此可以理解感官上的快感里满怀伤痛,但“蛇”对“我”的吸引毕竟是巨大的,抑或冰冷,“我”还是热望冰冷里藏着的“火炽”——或者是肉欲沉溺,但更有了一些精神需求的成分了。当然,也可能仅仅是“我”的一己幻想,“蛇”对“我”可能根本没有“磨光”或者“箍紧”的念想。“我”对“温暖”的期待是迫切的,而肉体的欲望彰显的是精神的诉求得不到或很难得到满足。我们从《蛇》这首诗的题旨可以看出它依然指向情欲的诱惑和罪恶,却没有了赤裸裸的肉感字眼,取而代之的是“蛇”的精美意象,充满了艺术的张力。最后两句借用了“云房”“冷宫”等古典元素,更是将西方的颓废观念和中国的古典意境完美地结合到了一起。
综观邵洵美的一生,年轻的他以为“诗是一座永久的建筑,自然界的一切是作诗最好的材料”。他要为诗、为文学奉献他的一生,在作为他两本诗集的序的那首诗的末句写道:“啊,不如当柴炭去燃烧那冰冷的人生。”人们评说他的诗“唯美,颓废”,但邵洵美并没有脱离生活的现实,在他活跃于文坛的20世纪30年代,正是日本侵华的年月。我们可以从他出版的刊物里,从他写的100多篇时事评论和编辑随笔里,看到他对国内外时局的关切,对日军步步进逼而国民党军队步步退让的不满,呼唤人们爱国抗敌。撕开他作品那层颓废的面纱,我们可以看到邵洵美内心燃烧的也是一个战斗者的激情。
三、空谷朝花:崔真吾的《忘川之水》
崔真吾(1902—1937),原名功河,字禹成,笔名真吾、采石、沙刹、史东,出生于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还是中学生的崔真吾参加了宁波中等学校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同时也使自己得到了一次精神洗礼。1924年崔真吾考入厦门大学。1926年参与创立了“泱泱社”,并主编文学刊物《波艇》,得到了当时在厦大任教的鲁迅的赏识,并从此一直保持着与鲁迅的密切交往。1928年冬,崔真吾与鲁迅、柔石、王方仁共同创办朝花社,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和版画。1929年起,崔真吾在宁波、广州、桂林等地辗转任教,其间组织热爱新文学的青年,参与进步运动,宣传无产阶级文学。1937年8月31日,遭国民党桂系反动派逮捕,9月15日深夜被秘密杀害。崔真吾的译著有史沫特莱《将军的戒指》、斯惠忒拉《接吻》,与鲁迅、柔石合译《奇剑及其他》等,诗集有《忘川之水》等。
崔真吾不仅是革命烈士,更是一位博学多才的诗人。他的诗集《忘川之水》由鲁迅亲自编校。诗人在《前记》里托词这本诗集是从海边一位青年的尸体旁捡到的,他依着青年的遗言将同时捡到的日记和相片放入棺中,却大胆地将这本诗集发表了。这篇有些离奇的《前记》为整个诗集蒙上了浪漫感伤的色彩。诗集中比较精彩的是前面的短诗,感情细腻,余韵绵绵。比如这首《后乐园里》:
不知怎的,上帝知道,
我只是凝视着她,
她只是凝视着我。
我笑了,她也笑了。
……
慷慨激昂的言论终归静寂。
十字街头我们大家分别——
她哟,还偷偷地回过头来。
抬头看,一颗明星远挂天际。
诗人从青年男女开始的一见钟情,到分别时的悄悄顾盼,将青年男女萌生爱意的过程表现得细致而又朦胧,那种青涩的淡淡的爱意在互相走远后的那一回眸中更加浓密,尤其是最后一句“明星远挂天际”,甚是富有象征意味,引人无限的遐思。
再看这首仅有四行的《再醮妇》:
在一条冷僻的狭窄的道上,
远远地她看了先夫生下的儿子。
走近他时她把阳伞下得低低些,
想遮没了她暗自流泪的面庞。
诗人将改嫁的寡妇见到先夫的儿子时的羞愧、关爱、痛苦、无奈的复杂心理,浓缩于一个动作——“把阳伞下得低低”和一个表情——“暗自流泪的面庞”,十分精妙,颇堪玩味。可惜“诗集后面的作品篇幅略长,但诗意反淡。大概是力所不逮” 。诗人用一个阳伞遮脸庞的动作把改嫁寡妇的那种既想看到儿子又羞愧见到儿子的复杂内心表现得淋漓尽致,让我们读诗的人在淡淡的哀伤中体味了这位改嫁妇人的内心。
。诗人用一个阳伞遮脸庞的动作把改嫁寡妇的那种既想看到儿子又羞愧见到儿子的复杂内心表现得淋漓尽致,让我们读诗的人在淡淡的哀伤中体味了这位改嫁妇人的内心。
崔真吾的作品数量虽不多,语言也简洁,但是感情充沛,用意绵绵,正如他的为人一样,真实、善良。胡兰成在他的书中曾赞扬崔真吾:“崔真吾姓的崔字就很美。他很会做事。暑假他回宁波,帮助种贝母的农民反对一位豪绅的垄断,官司打了几年,又发动农民焚香递呈,向当局请愿,才得到胜利。后来他相信唯物论,只因唯物论的宇宙与人事他觉得有一种清楚干净,当初反对豪绅,他原也没有着意于任侠,而后来做政治活动亦一般只是他的本性明朗正直。他仍旧遵守对爱人的约。他又有个堂姊姊,人相很俗气,说话的声音又难听,崔真吾见她被夫家离弃了,带她出来谋事不成功,一直维持她。崔真吾是希腊的,而他这种姊弟之敬却使人想起中国的礼,礼是不问对方如何,而只尽我的美意。朋友们为了崔真吾,见到这位姊姊也只得忍耐,而且觉得人与人真是该有在妍媸之外的相敬的。”
胡兰成在结尾中说:“这崔真吾,后来是在广西被黄旭初杀了。故乡白云天涯,惟有村前马樱花,春来向行人烂漫发满枝,那楼头少妇,做做针线又停了,想起他,只觉人世悠悠无尽,而又历历分明。” 当我们多年后翻开这位并不出名的宁波作家的作品时,正如胡兰成所讲,想起他,只觉人世悠悠无尽,而又历历分明。
当我们多年后翻开这位并不出名的宁波作家的作品时,正如胡兰成所讲,想起他,只觉人世悠悠无尽,而又历历分明。